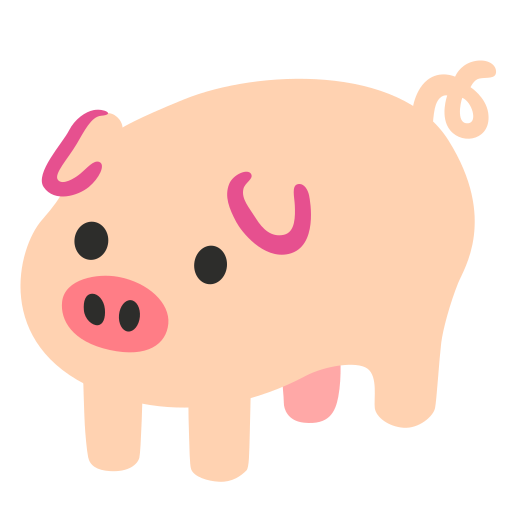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 镜中
编辑镜中
张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十年未见。
其实这是一个含混的说法。精确的数字,顾念从未费心去计算。时间一旦被赋予了具体的度量,便会获得一种物质般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心上。他宁愿让它保持模糊,如同一场年代久远的冬雾。
酒会设在滨江的一座美术馆里,巨大的落地玻璃之外,是城市冰冷的几何轮廓与江水破碎的灯火。衣着笔挺的男男女女,端着笛形的香槟杯,在一种程式化的、嗡嗡作响的温情里来回走动。空气中混合着酒精、高级香水与一种名为“社交”的无形物质的结晶体的味道。顾念对这一切感到厌烦,却又不得不置身其中。作为今晚唯一被邀请的“文化界人士”,他是一件活的展品,用以点缀这场资本游戏的精致与体面。
他看见江越,是在一片附和的笑声中。
那笑声如同潮水,而江越就站在潮水的中央,却又奇异地与周遭的一切分离。他穿着一套炭灰色的西装,剪裁无可挑剔,身形比记忆中更清减,也更挺拔,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反复淬炼过的刀锋。他正微微侧着头,听身边的人说话,唇角挂着一抹笑意,恰到好处的专注与礼貌,却不达眼底。那双曾像有火在烧的眼睛,此刻像两潭深水,表面平静,底下却不知藏着多少暗流与礁石。
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却是一种精心雕琢的痕迹。少年时那种不管不顾的、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燃烧殆尽的生命力,如今被收敛进一种更复杂、更沉稳的形态里。他成了一个标准的、成功的中年男人。一个陌生人。
就在那一瞬间,江越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目光越过人群,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顾念的身上。
四目相对。
整个美术馆的喧嚣,那些流动的光影,杯盏的脆响,嗡嗡的人声,仿佛在刹那间褪去了声音和色彩,只剩下一片虚无的白。顾念感到心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紧,不是疼痛,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剧烈的失重感。他以为自己会下意识地避开,但他没有。
江越也只是微微一怔,那平静的眼波似乎被投下了一颗石子,荡开一圈极轻微的涟漪,但随即又恢复了原状。他没有走过来,也没有显露出任何多余的情绪。他只是朝顾念的方向,将手中的酒杯举至与视线平齐的高度,隔着这十年的光阴与满堂宾客,遥遥一敬。
然后,他转过头,继续之前的话题,仿佛那只是一个投向无关紧要人的礼节性示意。
顾念也端起酒杯,将杯中那甜得发腻的液体一饮而尽。
酒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他毫无印象。回到位于南山半山腰的工作室时,已是深夜。他没有开灯,径直走到那面占据了整堵墙的巨大落地窗前。
窗外,城市的灯火在远方连成一片沉默的星海。而近处,是南山起伏的黑色轮廓,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山坡上种满了梅树,此刻,在冬夜的清辉下,只见其枯瘦嶙峋的枝桠,指向苍穹,如同无数双祈求或质问的手。
这里曾是一座废弃的气象观测站,他花了两年时间才改造成现在的样子。所有人都说他选了一个过于冷清的地方,但他喜欢这里的安静,尤其喜欢这扇窗。它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山景,也映照着他自己。
他脱掉外套,就着窗外的微光,坐在那张靠窗的旧沙发上。这是他常坐的地方。
他坐了很久,直到身体的寒意与窗外的夜色融为一体。
他想起了大学的游泳馆,那被氯水气息浸泡的、湿热的午后。想起了江越跃入水中时,那具年轻而矫健的身体划出的优美弧线。
他想起他攀上那座废弃瞭望塔的腐朽木梯,在塔顶的风中,像一只危险而骄傲的鸟。
他想起他最后一次见他时,那张因激动而微微发热的面颊,和他低下头时,那双羞惭又决绝的眼睛。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顾念闭上眼。窗外,仿佛有无数看不见的白色花瓣,在那无声的命令中,纷纷扬扬,开始飘落。起初是几朵,几片,继而,是席卷整个山峦的、一场沉默的雪。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