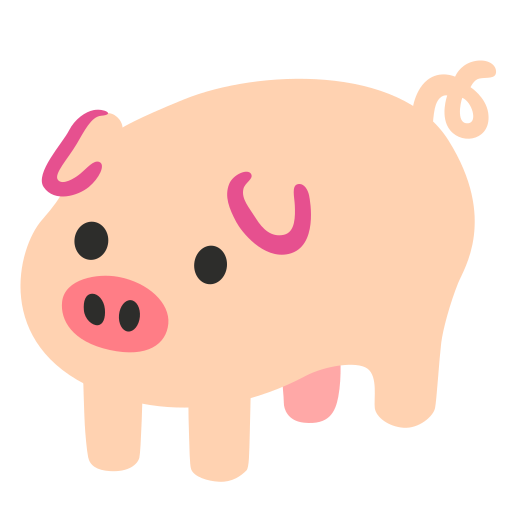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0/ 站台 告别
编辑那个暴力的雨夜像一场高烧,烧尽了他们之间所有激烈的情绪,只留下一片虚弱的、满是灰烬的废墟。
之后的一个星期,他们活在一种诡异的默契里,谁也没有再去找谁。李怀今每天在身体隐秘的酸痛和混乱的心绪中煎熬。他不敢去回想那个夜晚的细节,那些混杂着痛苦、屈辱和悲伤的纠缠像锋利的玻璃碎片,每一次触碰都会带来新的伤口。而陈东,则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李怀今知道,陈东内心的风暴一定比自己经历的更为猛烈。愧疚和自我憎恶,是比任何外在伤害都更残酷的刑罚。
就在这种死寂的沉默中,事情忽然迎来了转机,一个算不上光彩的转机。
陈东的父亲被放了出来。
理由是“证据不足”。那个唯一的目击证人,在公安局的几次问询下,说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最终翻了供,说自己当晚喝多了,看花了眼。而保卫科和公安局查了近一个月,既没有找到那批失窃的钢材,也没有发现任何销赃的渠道。这桩悬案,最终成了无头公案。
陈父虽然洗脱了罪名,但“嫌疑”这顶无形的帽子,却永远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他走在院子里,人们的目光比以往更加复杂,里面混杂着同情、猜忌和一丝“果然没本事才会被放出来”的鄙夷。清白,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解脱,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更深的社交泥潭。
在这个厂里,已经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
李怀今是在月考后的一个下午收到了陈东的消息。不是陈东亲自来的,是那个叫小五的混混,在校门口堵住了他,递给他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
纸条上只有几个字,是陈东那笔锋刚硬的字迹:明早七点,火车站。
李怀今的心像被一只手猛地攥紧。他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李怀今就瞒着父母独自一人去了火车站。三月的钢城,清晨的空气依旧冰冷。老旧的火车站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大量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南下打工的民工。这里充满了离别的气息,混杂着泡面的味道、廉价香烟的味道和柴油的味道,嘈杂而又伤感。
他在拥挤的候车大厅里找到了陈东。陈东也看到了他,对他招了招手。他身边放着一个破旧的帆布行李包,那是他全部的家当。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夹克,头发剪得很短,露出了饱满的额头。他看起来比几天前憔悴了很多,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但眼神却异常平静,那种毁天灭地的风暴似乎已经在他身体里平息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陈东的声音有些干涩。
“……你要去哪?”李怀今问。
“广东,”陈东说,“一个老乡在那边开了个小五金厂,介绍我过去。先干着再说。”
李怀今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所有的话语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那个晚上的阴影,依旧横亘在他们之间,让他们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然地对视。
“那天晚上……”陈东终于还是开口了,他别过头,不敢看李怀今的眼睛,“对不起。”
这三个字,他说得极其艰难,也极其真诚。
李怀今沉默了很久,久到陈东以为他不会再回答。然后,他才轻轻地摇了摇头,低声说:“都过去了。”
这不是原谅,也不是宽恕。这是一种超越了对错的、悲哀的理解。他明白,那天晚上的陈东和他自己一样,都是被那场巨大的、名为“时代”的风暴所裹挟、所伤害的牺牲品。
检票的广播响了起来,人群开始涌动。
“我得走了。”陈东站起身,背起了那个沉重的行李包。
李怀今跟着他,一路送他到检票口。在即将分别的那一刻,陈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被手心汗水浸得有些濡湿的纸条,塞到了李怀今手里。
“这是我打工那个厂的地址。虽然地方很破,但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他看着李怀今,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李怀今,你跟我不一样。你得好好读书,考出去,别再回来了。”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如果有一天……你在这边也待不下去了,就来找我。”
说完,他毅然转身,汇入了那片奔赴未知前程的、灰暗的人潮之中。
李怀今没有再跟过去,他只是站在原地,看着陈东的背影消失在站台上。很快,悠长的汽笛声响起,那列承载着无数人希望与绝望的绿皮火车,缓缓开动,带着“哐当哐当”的沉重声响,驶向了遥远的、温暖的南方。
他走了。带着一身的伤痕和疲惫,去为一个破碎的家,挣一个渺茫的未来。
李怀今独自站在空旷的站台上,直到感觉不到火车的震动。他缓缓摊开手心,看着那张被攥得皱巴巴的纸条。上面的地址字迹潦草,还沾着一点油污。
这是陈东留给他的一切。一个承诺,一个坐标,一缕在漫长寒冬里随时可能断掉的、脆弱的线。
他将纸条小心地、郑重地折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第一部,那场属于少年时代的、短暂而激烈的戏剧,落幕了。而他将独自一人,在这座日渐冰冷的城市里,迎来一个没有陈东的、真正漫长的冬天。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