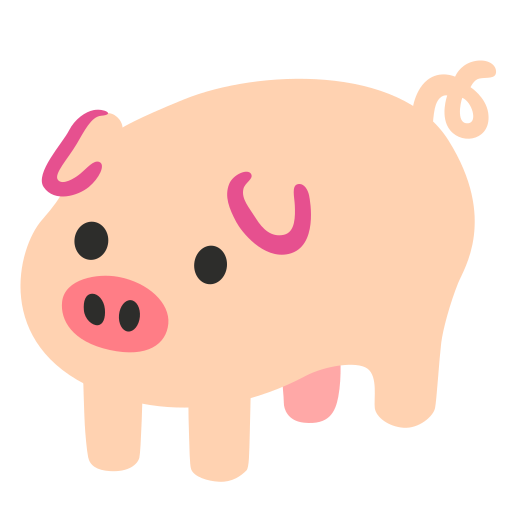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1/ 寂静 回响
编辑陈东离开后的日子像一条被拉长了的、灰色的静音轨道。火车带走了那个桀骜的少年,也带走了钢城最后一点喧嚣、野蛮的生命力。剩下的,是漫长到几乎能听到回响的寂静。
李怀今的生活被简化成了三点一线:家,学校,和偶尔在深夜独自一人前往的、那个废弃的平台。高三的学习压力如同一场无声的雪崩,将所有少年人的心事和精力都掩埋得严严实实。教室的墙上挂着鲜红的横幅——“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冰冷的数字将同窗变成无形的敌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睡眠不足的青色,像一株株被圈养在温室里、依靠输液管维持生命的植物,沉默地为着唯一的目标——高考——进行着光合作用。
李怀今一头扎进了这片由试卷和习题册构成的题海里。他用背不完的英语单词、解不完的数学公式、分析不完的古文来填满自己所有醒着的时间。这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当大脑被知识塞满时,就没有空隙去回味那个雨夜的疼痛,也没有精力去思念一个远在千里之外、杳无音信的人。
只有在深夜,当万籁俱寂,当台灯的光晕都显得疲惫时,那种蚀骨的思念才会像潮水般涌上来。他会他会戴上耳机,将Walkman里的磁带翻到B面,反复听着同一首歌。那是吴名慧的《心情电梯》,一个清冷而略带沙哑的女声,在寂静的夜里反复吟唱着起伏不定的心情。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本的夹层里拿出那张已经起了毛边的纸条。那串写在南方的、模糊的地址,是他与那个狂野却又真实的过去唯一的联系。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默读那个地名,想象着陈东在亚热带湿热的空气里,在机器轰鸣的工厂中,是何种模样。他是否也长高了?是否还像从前那样沉默寡言?他是否……会偶尔想起自己。
他开始像歌里一样盲目地每夜给陈东写信。
这是一种单向的、没有回音的倾诉。他不敢用家里的信封和邮票,而是跑去很远的邮局,买来最普通的信纸。他写学校里的事,写模拟考试的成绩,写那座废弃的工厂终于开始被拆除,写父亲日益花白的头发和母亲越来越频繁的叹息。他从不提及那个雨夜,也从不问陈东是否还记得他。他就那样一封一封地写着,仿佛在搭建一座跨越千山万水的、脆弱的纸桥。
他把写好的信,一封封锁进抽屉的铁盒里,一封也未曾寄出。他害怕自己的信会成为陈东的负担,更害怕那个地址早已失效,自己的满腔心事最终只会石沉大海。
那个属于他们的平台他依旧会去。只是如今,他成了唯一的访客。他会坐在陈东曾经坐过的位置,学着他的样子,让双腿悬在空中,俯瞰这座日渐陌生的城市。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筒子楼的外墙也因无人修缮而更加破败。这座城市,就像一个被掏空了内脏的巨人,只剩下一具空洞的、生锈的骨架。
他在这里,能清晰地感觉到陈东留下的回响。风声里,有他当年不羁的笑声;铁锈的气味里,有他身上淡淡的皂香;而脚下几十米的虚空,则永远提醒着他,曾经有一个少年在这里紧紧拉住了他恐高的手。
他和父亲的关系,陷入了一种客气而疏远的僵局。父亲李振宏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高考上。考出去,离开这里,去北京,去上海,成了父亲饭桌上唯一的话题。这既是期望,也是命令。李怀今默默地听着,从不反驳。他知道,这也是他自己的愿望。只是他想逃离的,除了这座衰败的城市,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巨大的秘密。
时间在无数张苍白的试卷中流淌而过。
六月七日,高考如期而至。整座城市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汽车禁鸣,工地停工,一切都在为这场决定无数年轻人命运的考试让路。李怀今走进考场,内心平静得如同一潭深水。过去这一年多的苦修,已经将他磨炼成了一台精准的答题机器。
两天后,当考完最后一门英语的铃声响起时,考场外瞬间被家长们的欢呼和拥抱所淹没。李怀今走出校门,看着眼前一张张激动而鲜活的脸,却感到一阵巨大的、无所适从的空虚。
他赖以逃避现实的堡垒,轰然倒塌了。
他没有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坐上了那趟通往市郊的、最破旧的公交车。他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爬上了那个锈迹斑斑的平台。
夕阳西下,将天边最后一片云彩染成壮丽的血红色。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早已被体温捂热的纸条,迎着风,只是望向遥远的南方。
高考结束了。少年时代,也结束了。接下来的人生,该往哪里去?那座纸桥的另一端,是否还有人在等待着一个渺茫的回响?
风从耳边吹过,带走了答案,只留下一片烈烈声。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