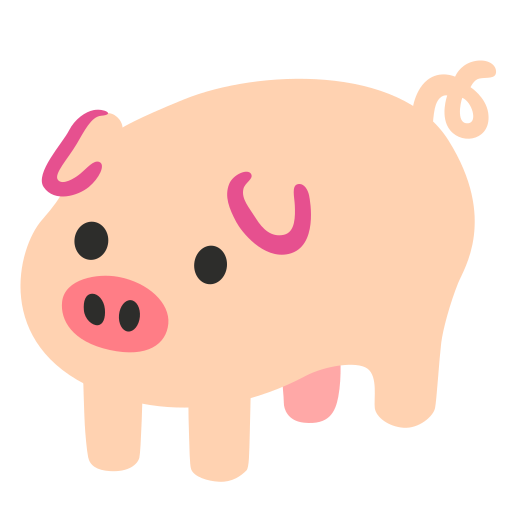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2/ 南国 苦旅
编辑在李怀今埋首于题海,用知识构筑抵御现实的堡垒时,陈东正赤身裸体地,被投掷进一个巨大、滚烫的熔炉里。
广东。
火车将他从一个冰封的、缓慢走向死亡的世界,带到了一个溽热的、野蛮生长的世界。走出车站的那一刻,一股混杂着海洋咸味、繁盛植物气息和工业废气的湿热空气,像一堵墙一样撞在他脸上。这里没有钢城那种辽阔而萧瑟的天空,天空被密密麻麻的握手楼、裸露的电线和巨大的广告牌切割得支离破碎。耳边是听不懂的、音调陡峭的粤语,眼前是拥挤得几乎没有缝隙的人潮。
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欲望和疲惫。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无数个像陈东一样的、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的流放地。
老乡介绍的五金厂,坐落在城郊一片无边无际的工业区里。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终日轰鸣的铁皮棚屋。空气里永远漂浮着刺鼻的金属粉尘和机油味。这里没有上下班的汽笛,只有冰冷的打卡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几十个工人挤在一间不通风的、弥漫着汗臭和脚臭的宿舍里。
这里遵循的是另一套丛林法则。拉长的呵斥、同乡之间的抱团与排挤、机器随时可能切掉手指的危险,共同构成了一个与钢厂大院截然不同的、更赤裸也更残酷的生态系统。
陈东在这里,像一棵被移植到陌生土壤里的、来自北方的树。他沉默、坚硬,用一身的刺来对抗着周围的一切。最初,有人见他年纪小,又是外地人,想欺负他。结果是在一次下工后的宿舍里,他用一把饭盆将一个试图抢他被子的老油条砸得头破血流。
那次之后,再没人敢轻易招惹他。他用最直接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他干活肯卖力气,脑子也转得快,很快就摸清了那些冲压机床的脾气。他像一头沉默的孤狼,在新的荒原上凭着本能和狠劲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他把每月工资的大半准时寄回家里。剩下的只够他最基本的生活。他戒了烟,因为那太奢侈。唯一的消遣,是偶尔去镇上的录像厅,花两块钱看一场枪林弹雨的香港警匪片。
他当然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同于在钢城时的那种孤傲,而是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无处附着的漂泊感。宿舍里,工友们在深夜里谈论着家乡的婆娘和孩子,谈论着发财后要盖什么样的房子。陈东从不参与,他只是躺在自己又硬又窄的铺位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念着北方的、那片冰天雪地里的一点微光。
他想念着李怀今。
这种想念,不像李怀今那样充满了诗意和辗转反侧的愁绪。对他来说,李怀今是他粗粝、灰暗的人生里,唯一柔软和明亮的所在。他会想起李怀今皱着眉头给他讲题的样子,想起他在高台上听着Nirvana时微微晃动的头,想起他身上干净好闻的、带着书卷气的味道。
这些记忆是他对抗这片钢铁丛林唯一的护身符。
他与那个世界的唯一联系是母亲定期寄来的家信。母亲的信里总是报喜不报忧,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安心工作,注意身体。但字里行间总会夹杂着一些钢厂大院的新闻。而陈东最渴望看到的,就是关于李怀今的消息。
“……总工家的那个怀今,今年要高考了,还是那么有出息,回回模拟考都是年级第一。他爸妈现在见人就笑,都盼着他能考上北京的好大学,给咱们钢厂子弟争光呢……”
母亲寥寥几句的闲笔,却是陈东反复阅读的重点。他能透过这些二手的信息想象出李怀今的生活轨迹——那个清瘦的少年,正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而奋斗。这个想象既让他感到安慰,又带来一种尖锐的刺痛。
他会给母亲回信,报平安,说自己一切都好,让他们别担心。但他从不敢在信里,哪怕是旁敲侧击地,询问一句关于李怀今的近况。那是一个他无法触碰的名字。他无法向母亲解释他们之间的纠葛,更无法将自己这一身泥泞,与那个正在通往“象牙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沉默,是他保护对方、也是保护自己最后一点尊严的唯一方式。
高考刚结束的夏夜,台风过境,工厂停工。宿舍里闷热得像蒸笼,陈东又一次爬上了天台。狂风卷着暴雨,天地间一片混沌。他迎着风,任由冰冷的雨水浇在自己滚烫的皮肤上。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个被塑料袋层层包裹的、母亲的信,借着远处工业区永不熄灭的灯火,又看了一遍那句“回回模拟考都是年级第一”。
他想,此刻的李怀今,应该刚刚结束了高考,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望着一片光明的未来。而他自己,则被困在这片南国的风雨里,前路不明。
他伸出手,迎向北方。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试图抓住什么,还是在告别什么。风雨声中,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站台,看着那张清秀而倔强的脸,在车窗外渐行渐渐远。
他们是两条奔向不同方向的河流,被巨大的山脉所阻隔。或许,最终都将汇入同一片名为“命运”的大海。但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各自的河道里,孤独地、日夜不息地,奔流。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