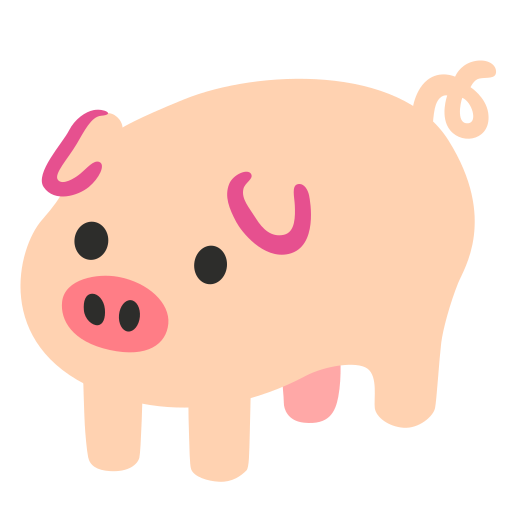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0/ 空白
编辑顾淮不知道自己在那个空房间里坐了多久。
他看着窗外的光线,从金色的午后慢慢变成橘红的黄昏,最终被深蓝色的夜幕彻底吞噬。镇上升起了炊烟,远处传来孩童的嬉闹声。人间烟火,一如往常。
只有他,被遗弃在了这个由真实历史与现实悲剧所构筑的真空里。
他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纸条,纸张的边缘已经被他手心的汗水浸润得有些濡湿。他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山上帐篷里,专家们因为那枚竹简而发出的兴奋赞叹声。
“改写文学史的发现!” “楚怀王与……与子期……这背后的宫廷秘闻,足以惊动整个史学界!” “顾淮,你是最大的功臣!”
功臣? 他想笑,却发现自己连牵动一下嘴角都做不到。
他穷尽自己的专业、直觉,甚至是灵魂,最终成功地为一段被埋葬千年的爱情举行了一场盛大而完美的出土仪式。他像一个最高明的修复师,将所有的碎片拼接完整,让一段绝美的历史重见天日。
可他亲手复原的,却是一座通往毁灭的纪念碑。
他向世人证明了那份爱有多么真实、多么深刻。 命运就用现实告诉他,那份爱的结局有多么不可更改、多么残忍。
历史,这个他曾用半生去热爱、去信奉的、严谨而公平的学科,在这一刻向他展现了最狰狞荒谬的一面。它像一个嗜血的古老神祇,接受了他虔诚的献祭,然后作为回报,冷酷地夺走了他唯一的、活生生的神女。
他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他不能再面对那座山,那座亭子,那些竹简。 他不能再做一个修复师。
因为他修复的每一段年轮,都在嘲笑着他的无能;他拼接的每一块残片,都在提醒着他的失去。
他要做一个与过去截然相反的人。 一个没有历史的人。 一个没有记忆的人。 一个……空白的人。
沈燃将自己烧成了“灰烟”,那么他,顾淮,就把自己活成一片“空白地”。
第二天的清晨,顾淮向项目组递交了辞呈。
他的理由很简单:个人健康原因,无法再继续工作。 面对张教授痛心疾首的挽留,面对考古队众人不解的追问,他一言不发。他拒绝解释,也拒绝告别。
在所有人眼中,他成了一个无法理喻的疯子、一个在事业最顶峰时因为某种神秘打击而彻底崩溃的天才。没有人能理解,为何在那个足以让他名垂青史的伟大发现之后,他选择的不是接受荣耀,而是彻底地自我放逐。
他平静地收拾好了自己那只简单的行李箱,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物。所有关于听雨亭的资料、图纸、研究笔记,他都原封不动地留在了桌上,仿佛那些东西从来就不属于他。
他坐上了那趟每日只有一班的、驶离云鹜镇的绿色长途客车。
车子缓缓开动,窗外,那片藏着听雨亭的黛色山峦渐渐向后退去。顾淮靠在窗边,却没有回头再看一眼。
他在心里,对那座山,对自己,也对那个不知在何方的沈燃,默念着:
“请你不要再听我了。” “我知道你在某处,隔风嬉戏。”
“空白地的梦中之梦,假的荷花……”
是啊,假的。 那段惊天动地的历史是假的,那场痛彻心扉的爱恋是假的,那个他以为可以殊途同归的约定,也是假的。 全都是假的。
当晚,他抵达了一座陌生又喧嚣的南方城市。 他站在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广场上,周围是闪烁的霓虹,嘈杂的广播,和无数张行色匆匆、与他无关的脸。
他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抽空。 情感,记忆,专业,身份…… 最后,连同那个名叫“顾淮”的自我,也一同被抽离了。
他站了很久,直到夜深。 他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饿。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他成了一个空洞的容器,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内容的空白。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