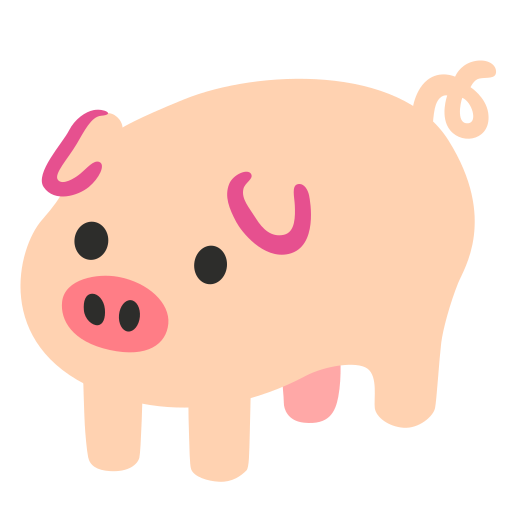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1/ 人间
编辑两年后。 南方,海滨城市。
顾淮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古籍部工作。
他的工作台靠着一扇终年不开的朝北的窗户。窗外是一株高大的白玉兰树,叶片浓绿,将本就不多的天光过滤得更加晦暗。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将那些破损、虫蛀、酸化得濒临死亡的古籍一页页地拆开,清洗,修补,再重新装订。
这是一个需要极致安静与耐心的工作,与他过去的人生有着一种遥远而讽刺的相似。
他修复历史。 但他不再相信历史。
他用一种近乎于自虐的、机械性的重复,将自己的每一天都填得满满当当。上班,下班,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一份便当,回到那间没有任何个人色彩的出租屋里吃完,然后睡觉。
他的睡眠很好,再也没有被任何梦境打扰过。 深沉的、无梦的、近乎于死亡的睡眠。 醒来后,是新的一天,继续重复前一天的内容。
他很满意这种生活。 这种被彻底“格式化”后空白的生活。
“顾淮”这个名字连同他身上所有与“修复师”、“天才”、“听雨亭”相关的标签,都死在了两年前那个离开云鹜镇的清晨。现在活着的,是“顾先生”。一个沉默寡言,背景不详,在人群中不会被任何人多看一眼的、图书馆的普通职员。
同事们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他从不参加任何聚会,也从不与人闲聊。有一次部里新来的研究生拿着一本关于楚国漆器纹样的图册向他请教,他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了解”,便转身走开了。
他像一只受过重伤后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警惕的刺猬。他用冷漠和疏离包裹着自己,拒绝任何可能触碰到他内在“空白”的企图。
只有一次,他失控了。
那天,他在整理一批新入库的考古期刊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标题——《楚云梦听雨亭遗址‘子期’竹简考辨》。
他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滞了。
他不受控制地翻开了那篇论文。上面印着他无比熟悉的亭台的测绘图,以及那枚关键竹简的高清照片。论文的作者,是张教授和王老师。他们在文章的引言部分提及了项目的“前任负责人顾淮先生”,说他“以其惊人的艺术直觉为本次发现提供了决定性的方向,后因个人身体原因遗憾退出,但其贡献不可磨灭”。
文章写得很客观,也很严谨。它将那段惊天动地的、关于神女或是伶人的爱情秘闻,变成了一段段可以被引用的冷静的学术文字。 一个持续了两千年的活生生的悲剧,最终,成了一篇可以用来评定职称的完美论文。
顾淮放下期刊,冲进了洗手间。
他撑着冰冷的水池剧烈地干呕起来。他什么都吐不出来,只有胃部深处传来一阵阵痉挛的、尖锐的痛楚。他看着镜子里那张苍白而陌生的脸,第一次,对自己这种“空白”的人生,产生了无法遏制的怀疑。
他以为他埋葬了历史。 原来,他只是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历史的孤坟。
那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刻意避开考古类的书架。他以为只要不看,不想,那些被他强行压抑下去的东西就不会再出来作祟。
他像一个行走在人间,却没有影子的鬼魂。 他呼吸,他吃饭,他工作,但他没有“活着”。
他以为,这就是他余生的全部。 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安全的、也毫无生气的空白里,缓慢地、安静地,等待着真正的死亡降临。
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窗外下起了连绵冰冷的秋雨。 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一首歌。 一首,来自他坟墓之外的、带着火焰温度的歌。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