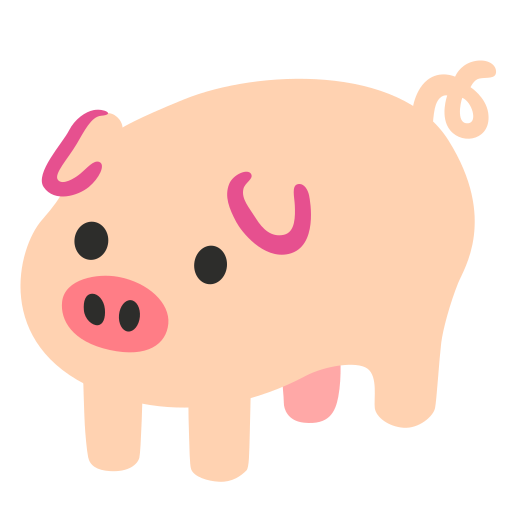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2/ 雨滴
编辑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冬日,没有雪,只有连绵不绝的冰冷细雨。图书馆里没什么人,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暖气混合的、催人昏昏欲睡的气味。角落里的老式收音机正播放着一个独立音乐电台的节目,DJ的声音慵懒,像窗外的雨一样,无休无止。
顾淮正低头修复一页破损的宋版书,用竹制的压条小心地抚平纸张上的褶皱。他的世界已经缩小到了眼前这张工作台的大小。安静,可控,绝对安全。
就在这时,一首歌毫无预兆地闯入了他的耳朵。
没有前奏,一段狂暴而精准的贝斯solo,像一把淬了冰的锋利匕首,瞬间刺破了室内沉闷的空气。那段旋律,充满了复杂的、不协和的和弦,却又带着一种摇摇欲坠的奇异美感。它野蛮,乖张,充满了不被驯服的生命力。
顾淮的手猛地停住了。
竹压条从他指间滑落,掉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啪”的一声。
他缓缓地抬起头,像一尊被声音击中的石像一动不动。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用这种方式弹奏贝斯。像在与乐器搏斗,又像在与整个世界为敌。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血和汗的味道。
是沈燃。
紧接着,一个沙哑如被烟酒浸泡过的、却又无比熟悉的声音唱了起来。歌词很简单,颠三倒四,像醉酒后的胡言乱语。
“……捡到一场雨/淋湿了火/火说它不疼/灰烬在说谎……”
“……造了一座亭/关住了风/风说它不怕/门忘了上锁……”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滚烫的雨滴砸在顾淮早已冻结成冰的心湖上。溅起的不是涟漪,而是钻心刺骨的痛。
他以为自己早已成了一堆不会痛的冰冷灰烬。 可这首歌,却像一个来自远方的、恶毒的谶语,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他: 你在说谎。
他丢下手中所有的工作,踉跄地站起身,冲到那台老旧的收音机旁,像是要确认什么。电台的DJ在那首歌结束后,用一种慵懒的语调说:“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来自‘空白地’乐队的歌曲,《灰烬说谎》。一支非常神秘的乐队,从不接受采访,也从不参加任何音乐节,只用作品说话。主唱兼贝斯手‘燃’的编曲,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空白地。 燃。
顾淮靠着冰冷的书架,缓缓地滑坐在地。
他笑了。那是一种比哭泣更绝望的、无声的笑容。
他花了两年时间将自己活成了一片“空白”。 而沈燃却用这两年时间,将他们之间那片共同的、无法被填补的废墟命名为了“空白地”。
他们从未分开过。 即使隔着千山万水,即使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也依旧被囚禁在同一个名字的巨大牢笼里。
那首歌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用两年时间精心构建的记忆囚笼。云鹜镇的潮湿,工棚里的暴雨,那张写着“保重”的纸条,那个在晨光中脆弱的睡颜……所有被他强行掩埋的画面,在这一刻,都挟裹着巨大的声浪呼啸着向他席卷而来。
他捂住脸,肩膀开始无法抑制地颤抖。 不是哭泣,而是一种在极致的痛苦中,身体的自然痉挛。
他终于明白,他的逃离,他的自我放逐,是多么的愚蠢和徒劳。他以为自己是在保护,殊不知这种保护对沈燃而言,才是最残忍的抛弃。他亲手将沈燃,一个人,留在了那片燃烧着过往的痛苦废墟里。
而沈燃,这两年来一直在用他的音乐发出求救。 不,那不是求救。 那是在呐喊,在质问,在挑战。 他在问他:顾淮,你听到了吗?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重新站起身。他走回自己的工作台,没有再去碰那本宋版书,而是拿出手机。他的手指因为太过用力而有些发白。
他在搜索框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了乐队的名字。
“空白地”。
屏幕亮起,无数条信息涌现出来。乐队的介绍,几首小范围流传的单曲,以及……一张即将结束的、全国Livehouse巡演的海报。
海报的设计很简单,黑色的背景上,是一团白色的、模糊的火焰。
最后一站的城市名字,像一个等待了他两年的、无法回避的审判,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 正是他如今所在的这座,多雨的城市。
时间:下周五,晚八点。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