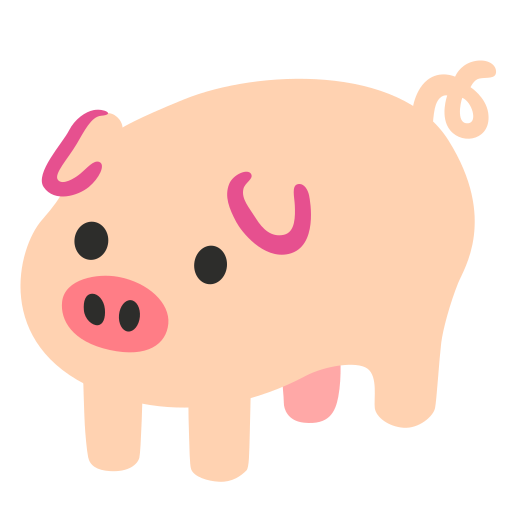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3/ 地址
编辑从下周五到这周五不过是七天。但对顾淮而言,这段时间远比过去那空白的两年要漫长得多。
他请了假,将自己重新关进了那间临街的出租屋里。他无法再去图书馆,无法再面对那些沉默的、需要被修复的故纸堆。因为他发现,他自己才是那个最残破、最需要被修复的人。
他的失眠症以一种报复性的姿态卷土重来。
但这一次,他梦见的不再是那个遥远的、隔着雨幕的楚王。他梦见的全是沈燃。是沈燃在酒吧里那个挑衅的笑,是沈燃被雨水打湿的、贴在额角的黑发,是沈燃在工棚里覆在他身上时滚烫的体温和剧烈的心跳。这些属于“今生”的、无比真实的碎片,远比那个属于“前尘”的、宏大的悲剧更令他痛苦。
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听“空白地”乐队的歌。
他把网上能找到的五首歌循环播放,直到每一个音符都刻进他的骨头里。他用一种近乎于考古解剖的、病态的专注去分析沈燃的音乐。
他听懂了。
那狂暴的贝斯,不仅仅是在宣泄痛苦。那是在反抗,是在与一个名为“命运”的无形敌人搏斗。那些破碎的、颠三倒四的歌词,是在用一种现代人戏谑而绝望的语言,去重述那个古老的、关于“神女”与君王的故事。
“他们给我/画了一张脸/说我住在云里面”,这是在嘲笑那个“神女”的谎言。 “我的亭子/没有屋顶/我的火/从不为谁熄灭”,这是在宣告,他拒绝被囚禁、也拒绝被定义。
顾淮终于明白,沈燃这两年不是在自怨自艾地舔舐伤口。 他是在用他唯一懂得的、也是最擅长的方式,进行一场一个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他在对抗那个想要将他拖回过去的巨大的历史阴影。
而自己,却懦弱地在这场战争中当了整整两年的逃兵。
“令我彻夜难眠的住址”。
那个Livehouse的名字和地址,像一个带着诅咒的发光符咒,占据了他全部的思维。他上网查过,那是一个很小的、藏在城市某个旧工业区里的地下音乐场所。地图上的那个红色标记点成了他世界新的中心。
他害怕那个地址。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沈燃。他该怎么开口?说“你好,好久不见。顺便说一句,我俩的前世,是一段被写入《高唐赋》的宫廷秘闻”? 这太荒谬了。这真相沉重得足以压垮任何人。 他害怕这真相,会成为他和沈燃之间一道新的、永恒的深渊。
他甚至想过,就这样算了吧。就假装自己从未听到过这首歌,假装自己还是那个活在“空白”里的顾先生。远远地,听着沈燃的音乐,知道他还活着,还在燃烧,或许就足够了。
可是他做不到。
因为他从沈燃的音乐里,听到的不仅是反抗,还有一种被掩藏在最深处的孤独。 沈燃在与命运搏斗。 但他需要一个战友。
周四的晚上,他鬼使神差地坐公交车去了那个地方。
Livehouse还没开始营业,黑色的铁门紧闭,像一张拒绝交流的嘴。门口贴着“空白地”巡演的海报,那团模糊的白色火焰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格外孤寂。
顾淮就站在街对面,隔着一条马路静静地看着那扇门。 他想,子期的悲剧,在于他无法选择。 而他顾淮,现在有的选。
他可以选择继续躲在自己的坟墓里,让沈燃一个人去重复那个伶人注定陨落的宿命。 他也可以选择推开眼前这扇门,走进去。无论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是拥抱还是拒绝,是救赎还是共同毁灭,他都要和他站在一起。
像两千年前,那个叫熊今的楚王,在叛军围城的最后一夜依旧选择走进听雨亭,与他的伶人站在一起一样。
周五晚上,七点四十五分。
顾淮站在Livehouse的门口。这一次,铁门大开,里面传出嘈杂的人声和设备调试的巨大声响。年轻的、穿着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三三两两地聚集在门口抽烟、说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青春、酒精和荷尔蒙混合的气味。
顾淮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深色风衣,站在这群人中间,像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纪的、格格不入的幽魂。
他买了一张票,检票员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在他手背上盖了一个荧光的章。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两年前,云鹜镇那个雨夜的潮湿。
然后,他推开那扇厚重的、隔着两个世界的门,走了进去。 他要去奔赴的,不仅仅是一个人。 更是一段等待了他两千年的——宿命。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