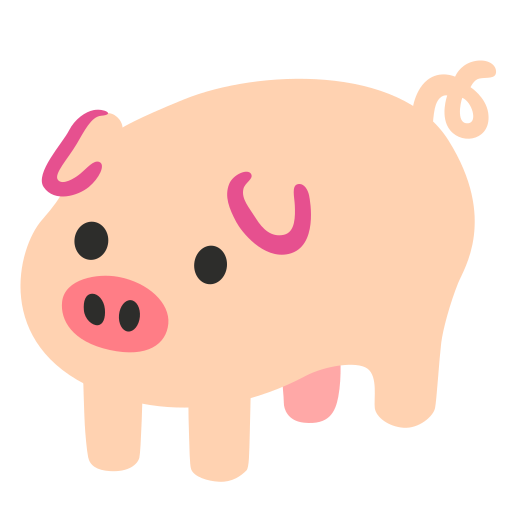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4/ 归途
编辑Livehouse内部是一个被声音和黑暗包裹的洞穴。
空气浑浊,光线暧昧,巨大的音浪像海啸一样反复冲刷着每个人的身体。舞台上还没有人,但人群已经开始躁动,像一场风暴来临前的蚁群。
顾淮被这股人潮推搡着,挤到了一个相对靠后的、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角落。他像一个异物,被这片沸腾的海洋所包裹,却无法融入其中。他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不是因为音乐,而是因为一种近乎于怯懦的期待。
他两年没有见过沈燃了。 他不知道时间和那段沉重得足以压垮任何人的历史会把他变成什么样子。
不知过了多久,场内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人群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一片黑暗中,只有手机屏幕的光,像无数点鬼火在晃动。
然后,一束惨白色的追光猛地打在了舞台中央。
沈燃就站在那里。
他穿着一件最简单的黑色T恤,头发比两年前更长了些,随意地在脑后扎成一个小揪。他依旧很瘦,但肩膀的线条似乎更宽阔了一些,不再是少年那种单薄的姿态。他怀里抱着那把伤痕累累的贝斯,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他比顾淮记忆中要安静得多。像一团燃烧过后,正在缓慢冷却的炭火。
乐队的另外两名成员也走上了台,灯光渐亮。
沈燃走到麦克风前,依旧没有抬头。他只是用手指轻轻拨动了一下琴弦,发出一个低沉的、试探性的音符。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最后一站了。”他开口,声音沙哑,透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场地,“巡演结束,乐队也该……休息了。谢谢大家。”
他的话很短,像一句仓促的告别。说完,他便不再言语,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闭上了眼睛。
下一个瞬间,狂暴的音乐毫无预兆地炸裂开来。
是那首《灰烬说谎》。
现场的版本,比录音室里要粗粝一百倍,也绝望一百倍。沈燃的贝斯像一头失控的困兽,在嘶吼,在冲撞。而顾淮,在这片巨大的、混沌的音墙之中,第一次听懂了这首歌真正的语言。
那不仅仅是一首歌。 那是一场复仇。
那狂乱的鼓点,是两千年前叛军攻城的马蹄声。 那撕裂的吉他,是朝堂之上百官攻讦的谗言。 而那段时而呜咽、时而暴怒的贝斯,是君王被围困在听雨亭中,那种无能为力的、爱与恨交织的绝望心跳。
这是沈燃,在替那个无法为自己辩解的子期,在替那个被污蔑为“男祸”的伶人,向这个世界发出迟到了两千年的呐喊。
顾淮站在人群的最后方,遥遥地望着舞台上那个近乎自毁的身影。他的耳朵被巨大的声浪震得发麻,但他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只看得到沈燃。
他看到沈燃紧闭的双眼,看到他紧绷的、青筋凸起的脖颈,看到他汗湿的头发粘在脸颊上。他甚至能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混杂着痛苦与狂喜的、极致的孤独。
“……火说它不疼/灰烬在说谎……”
当唱到这句歌词时,沈燃猛地睁开了眼睛。他抬起头,目光像两道锋利的探照灯越过所有狂热的脸孔,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那目光里带着一种不抱任何希望的、习惯性的绝望。
然后,他的目光与角落里的顾淮撞在了一起。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所有的声音,所有的人群,都在瞬间褪去。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一个是被世人围观的“神女”,一个是跋涉了千年才找到他的“君王”。
四目相对。
顾淮看到,沈燃的眼中那层伪装出来的、燃烧般的疯狂,在一瞬间寸寸碎裂。露出了底下无边无际的悲伤与震惊。像一个流亡了两千年的魂灵,终于在异乡的街头看到了故国的来人。
他的嘴唇在无声地翕动。
顾淮读懂了那两个字。
他说的是:“顾淮。”
一滴滚烫的液体毫无征兆地从顾淮的眼眶中滑落。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自己还会流泪。他还以为自己早已干涸成了一堆不会哭的灰烬。
“人同道殊,而殊途同归”。
他终于明白了这句诗真正的含义。
他们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选择自我放逐,在喧嚣的音乐中,为历史翻案;一个选择自我囚禁,在死寂的沉默中,惩罚自己。
但无论道路如何不同,他们最终还是在这一刻,抵达了同一个终点。 那就是再也无法掩饰的,对彼此的渴望。
音乐在最激烈处戛然而止。 沈燃将贝斯从身上摘下,重重地放在了地上。那一声巨响像一个休止符,结束了所有纷乱的乐章。也像两千年前那根在烈火中断掉的琴弦。
他一言不发地,在全场观众错愕的目光中走下了舞台。
他没有走向后台,而是径直穿过拥挤的人群,朝着顾淮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人群像摩西眼前的红海,自动为他分开了一条通路。
他就这样走到了顾淮的面前。
两人相顾无言。 周围的喧嚣似乎都被一个无形的罩子隔绝在外。他们只能听到彼此剧烈的心跳和呼吸。
沈燃的身上全是汗水和烟草的味道。他喘着气,胸膛剧烈地起伏,眼眶是红的。他看着顾淮,像在看一个失而复得的、破碎的梦。
“我以为……”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几乎不成样子,“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顾淮伸出手,用一种近乎于颤抖的动作,轻轻地拭去了沈燃脸颊上的一滴汗水。那触感滚烫而真实。
“我来接你,”他说,声音里带着两年的风霜和一生的笃定,“回家。”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