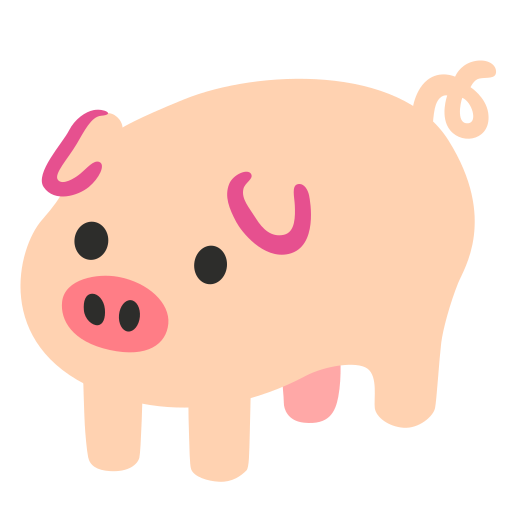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5/ 热泪
编辑“家”这个字对沈燃来说是一个绝对的禁忌。它代表了他生命里全部的缺失与背弃。
但当这两个字从顾淮的嘴里,用一种无比郑重的、带着两年风霜的笃定语气说出来时,沈燃感觉自己用坚硬外壳包裹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在那一瞬间彻底崩塌了。
他没有回答。
他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
他伸出手,紧紧地、近乎于粗暴地,抓住了顾淮的衣袖。然后拉着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充满了喧嚣与回忆的Livehouse。他把整个乐队和一场尚未结束的演出都抛在了身后。
他们什么都没带,就这样走入了城市冰冷的、下着细雨的深夜里。
雨丝很密,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霓虹灯的光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晕染成一片片模糊而破碎的色块。他们没有说话,只是并肩走着。沈燃依旧紧紧地抓着顾淮的衣袖,像是怕他会突然消失一样。
他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穿过了无数个红绿灯,路过了无数张陌生而漠然的面孔。最终,顾淮带着他,回到了自己那间临街的出租屋。
那是一个很小的、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地方。与云鹜镇那间冷静到近乎刻板的屋子不同,这里有没来得及洗的碗,有随意搭在椅子上的外套,有从窗缝里飘进来的、属于人间的饭菜香味。
这里不像一座需要用生命去守护的华美的听雨亭。 这里更像一个普通人的、可以被称为“家”的地方。
顾淮给他找了一条干毛巾,又倒了一杯热水。沈燃接过,却没有喝,只是用手心包裹着那杯子的温度。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依旧是沉默。但这种沉默不再是充满了试探与戒备的对峙。而是一种风暴过境后尘埃落定的安宁。
“我怕。”
沈燃最终先开了口,他低着头,声音很轻,像在对自己,也对那个古老的亡魂忏悔,“我感觉得到……那个故事。它的结局,是火。我以为,只要我跑得够远,那场火就烧不到你身上。”
顾淮静静地听着,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终于确认,沈燃也和他一样,一直背负着那个沉重的、来自前尘的记忆。
“我回去过,”顾淮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足以穿透时空的重量,“回到了那座亭子。我找到了证据。”
他将那枚竹简的发现,将那个关于“神女”的、被精心编织了两千年的谎言,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沈燃。他告诉他,他们的爱不是一段被诅咒的禁忌,而是一段强大到足以让后世文人为它创造出一个神话来作掩护的真实。
沈燃听着,身体开始无法控制地微微颤抖。
“所以呢?”他抬起头,眼眶红得像要滴出血来,“那又怎么样?证明了又怎么样?子期的结局还不是和楚王一起,烧死在了那座亭子里?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不该在一起!”
这是他逃亡了两年的、所有恐惧的根源。他害怕的是那个早已被写好,不可更改的悲剧结局。
“不。”顾淮看着他,目光坚定而清澈,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历史不是一本需要我们去盲从背诵的剧本。它是一本……写满了答案的错题集。”
他伸出手,捧住了沈燃的脸,强迫他看着自己。
“熊今和子期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们相爱了。而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无法容纳他们爱情的时代。熊今的错,在于他是个王,他有他放不下的江山。子期的错,在于他太爱那个王,爱到愿意为他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最后再和他一起化为灰烬。”
顾淮的指腹,轻轻摩挲着沈燃冰冷的脸颊。
“可是沈燃,你看看我们。”他的声音温柔而有力,“我不是王,我没有需要用你去交换的江山。而你,”他凝视着沈燃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不是那个需要被藏起来的神女。你是一个会把贝斯弹得震天响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摇滚乐手。”
“我们活在一个……可以选择的时代。我们可以写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结局。”
沈燃的防线在这一刻全线崩溃。
两年的逃亡,两年的自我放逐,两年与宿命的独自对抗,所有的坚硬和伪装,都在顾淮这番话面前,被彻底击碎。
一滴滚烫的眼泪毫无征兆地从他眼角滑落,滴在了顾淮的手背上。那温度比火焰更灼人,比千言万语更滚烫。
那是神的热泪。 是一个流亡了两千年的、孤独的灵魂,终于卸下了神女的面具,允许自己作为一个凡人被拯救时,流下的第一滴眼泪。
“我……”沈燃的声音哽咽,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把乐队解散了。我……无处可去了。”
顾淮收紧了手,将他冰冷的手指,一根一根地,纳入自己的掌心。
“那就留下。”他说。 “我们哪儿也不去了。”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乌云散去,一轮清冷的、残缺的月亮,从云层后面露了出来。月光透过窗户,洒进这间小小的屋子,将两个相互依偎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