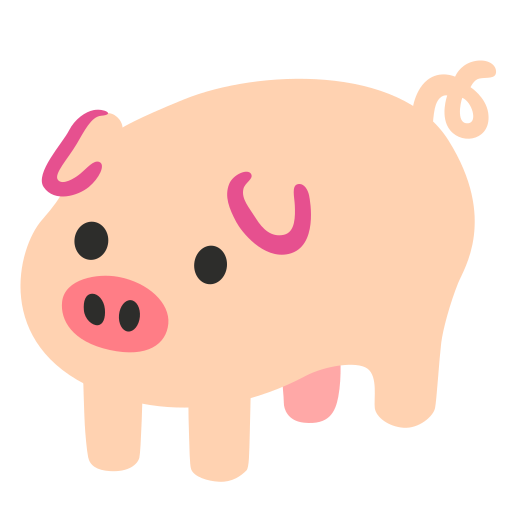4/ 春夜
编辑考古与修复的现场,是一处被强行打开的时间剖面。
听雨亭坐落在半山腰,四周被高大的竹林环绕,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天然围场。山体滑坡的痕迹依旧触目惊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巨大伤疤。明代的亭子主体尚存,但歪斜欲倒,檐角如垂死的鸟首,无力地指向天空。而在它被撕裂的基座之下,考古队已经清理出了一片近百平米的区域,属于战国晚期楚国的夯土台基,沉默地袒露在空气中。
顾淮的工作,就是在这两个相隔近两千年的时空断层之间,试图建立一种秩序。
他每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戴着安全帽和手套,与测绘图纸、结构数据和沉默的木石打交道。他的团队由几个经验丰富的本地工匠和两名年轻的实习生组成,他们都对这位年轻、沉默、要求严苛的顾老师敬而远之。他身上那种近乎于洁癖的专业主义,与这里泥泞、混乱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沉浸在这种对抗性的工作中。每当他用探针精准地找到一处隐藏的卯榫,或是根据腐朽的痕迹推断出一段梁木的原貌时,他都能获得片刻的、掌控一切的满足感。这是一种与梦境截然相反的体验。在这里,他是解构者与重建者;而在梦里,他只是一个被动的、失语的囚徒。
那天傍晚,团队的其他人已经收工下山,顾淮独自留了下来。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主梁的一处榫卯结构因为长期的雨水侵蚀和地质位移,发生了肉眼难见的形变,导致所有的修复方案在计算机模拟中都出现了偏差。他必须在现场进行最原始的、依赖于手感和经验的勘测。
暮色四合,山林间的雾气开始升腾,像缓慢涨起的潮水。他打开了高功率的作业探灯,一道惨白的光柱刺破薄暮,将残破的亭台勾勒成一具光影交错的巨大骨骼。四周的虫鸣声渐渐响亮起来,衬得他所在的光圈之内愈发寂静。
他正戴着手套,用指尖细细地触摸着那处腐朽的木料,试图在朽坏的纤维中感知它最初的形态,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不疾不徐,踩在泥土和碎石上,发出一种笃定的、毫不掩饰的声响。
顾淮直起身,回头望去。
沈燃就站在光圈的边缘,一半身体在光明中,一半隐在黑暗里。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罐啤酒和一盒尚有余温的食物,像是刚刚从镇上的夜宵摊买来的。
他看着顾淮,脸上没有丝毫意外,仿佛他早就知道他会在这里。
“还不下班?”沈燃的声音在空旷的山野里显得很清晰,“打算在这里修仙吗?”
顾淮皱起了眉。这里是封闭的工作区域,外人禁止入内。他不知道沈燃是怎么上来的。但更让他感到烦躁的,是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与世隔绝的工作氛围就这样被轻易地打破了。
“你怎么上来的?”他问,语气冰冷。
“山又没长腿,走上来的呗。”沈燃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朝他走近,“看你这儿灯亮着,猜你没吃饭。喏,镇上最好吃的烤串。”
他将食物和啤酒放在一块相对平整的石板上,自顾自地打开一罐,金属拉环发出一声清脆的“噗”响。他没有递给顾淮,而是自己先灌了一口。
顾淮看着他,没有动。他无法理解这个人的行为逻辑。他们之间不过是两面之缘,一次不愉快的对视,一场更不愉快的对话。这种自来熟的、毫无边界感的侵入,让他感到极度不适。
沈燃似乎毫不在意他的冷漠。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那残破的亭子和裸露的地基,眼神里没有游客式的好奇,也没有对文物的敬畏,而是一种更私人的、仿佛在打量某个老朋友的眼神。
“这地方,”他开口,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一些,“挺能睡的。”
顾淮愣了一下,没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说,躺在这里,应该能睡个好觉。”沈燃用下巴指了指那片楚国地基,“比任何床都安稳。”
这是一种完全颠覆顾淮认知体系的感受方式。在他眼里,这里是数据,是历史,是亟待解决的结构问题。而在沈燃的感知里,它是一个有情绪的、可以与之对话的场域。
“你不懂。”顾淮最终还是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捍卫领地般的固执。
“我是不懂你们那些条条框框,”沈燃笑了,露出白色的牙齿,“但我知道,有些木头会哭,有些石头会等人。这地方,等了很久了。”
就在这时,毫无征兆地,雨滴落了下来。
最初是几滴,砸在安全帽上,发出“嗒、嗒”的声响。紧接着,雨势骤然变大,密集的雨点连成一片,像一张巨大的、正在收拢的网。山风呼啸而来,卷起竹林的涛声。
“操。”沈燃低骂一声,拉起顾淮的手腕,就朝亭子最完整的那一角跑去。
那只手掌心滚烫、干燥而有力,与顾淮自己微凉的体温形成鲜明对比。顾淮几乎是被他拖拽着,躲进了那个只能勉强遮蔽风雨的角落。
一时间,世界只剩下了雨声。雨水敲打着残存的瓦片,汇成水流从破损的檐角淌下,在他们面前形成一道道不规则的水帘。探灯的光线穿过雨幕,被切割、折射成无数晃动的光斑。他们被困在这座时间的孤岛上,与外界彻底隔绝。
刚才的剑拔弩张,似乎被这场大雨冲刷掉了。沈燃靠着一根幸存的立柱坐下,又打开一罐啤酒。这一次,他递给了顾淮。
顾淮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冰冷的罐身让他因为被强行触碰而有些僵硬的手指,恢复了一点知觉。
“我也有个梦。”沈燃突然说,他看着眼前的雨帘,声音被雨声包裹着,显得有些模糊。
顾淮握着啤酒罐的手指收紧了。
“挺没劲的。”沈燃自嘲地笑了笑,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趣闻,“总梦见自己在一片黑漆漆的地方,怎么也走不出去。然后就会看到一只飞蛾,白色的,会发光。我就跟着它跑。那傻逼飞蛾,每次都飞到同一个地方,落在一个男的肩膀上。那男的穿着古代的衣服,看不清脸,总是在叫一个名字。可我每次都听不清。”
他仰头喝了一口酒,继续说:“你说好笑不好笑?跟演电视剧似的。”
顾淮没有笑。他感觉自己的血液,在那一瞬间,似乎停止了流动。
西边的飞蛾。 那个一直轻呼我名字的人。
诗句,像被唤醒的亡魂,在他脑中轰然作响。
他的梦,是楚王梦雨,是宫殿春夜的独酌。 他的梦,是水腰绢帛,是空亭吐纳的云雾。
而沈燃的梦,是幽居的辞别,是探听虚实的飞蛾。
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梦境碎片,在此刻,因为一场真实的雨,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了一起。它们指向同一个故事,同一个被遗忘的地址。
顾淮猛地看向沈燃。对方正专注地看着雨,侧脸的轮廓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异常柔和。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投下了一颗怎样惊世骇俗的炸弹。他只是单纯地,在一个被雨困住的夜晚,分享了一个无聊的梦。
雨势渐渐小了。
沈燃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将空啤酒罐精准地扔进不远处的垃圾袋里。“走了。”他像来时一样突兀地告别。
他走出亭子,几步就消失在雨后的夜色里。
顾淮独自一人久久地站在原地。四周又恢复了寂静,只有雨水从屋檐滴落,发出富有节奏的声响。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中那罐未开的啤酒,上面还残留着沈燃手指的温度。
他忽然明白了。
这座亭子,这片遗址,对他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份工作。 它是一个地址。 而那个一直轻呼他名字的人,已经出现。
梦境,不再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了。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