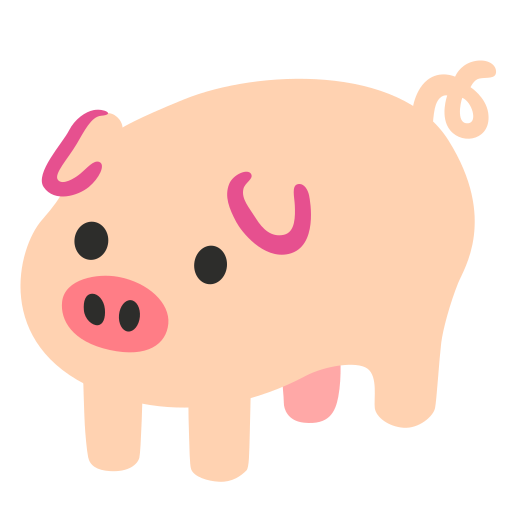3/ 闻脉
编辑顾淮以为,与那个年轻人的相遇,不过是旅途中一次意外事件,一段与他主旋律无关的嘈杂变奏。他可以轻易地将它过滤、遗忘,像删除一段错误的音频文件。可他显然高估了自己对生活的编辑能力。
几天后,他在镇上唯一那条贩卖日常用品的街上,再次见到了沈燃。
当时是下午,太阳难得地从云层的缝隙中挤出来,给潮湿的青石板路镀上了一层短暂而脆弱的金色。顾淮正在一家杂货铺里购买几样必需品,他专注地辨认着货架上那些包装简陋的商品,试图在有限的选择里维持自己一贯的生活标准。
“喂。”
一个声音从他身后响起。很近,带着一丝刻意的沙哑,像砂纸摩擦过粗糙的木面。
顾淮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他不需要回头,就已经辨认出了声音的主人。那种侵略性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白天,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庸常环境里,也依旧锋利如初。
他没有理会,拿起一包盐,转身准备去付账。
沈燃就站在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白天的他,褪去了舞台灯光的迷幻,显得更为真实,也更具冲击力。他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色背心,露出结实而流畅的臂部线条,纹身在日光下呈现出更清晰的细节。他的皮肤是一种常年被阳光和酒精浸泡后的小麦色,眼神依旧是亮的,带着一种野生的、未被驯化的神采。他斜倚着货架,双手插在裤袋里,姿态是一种全然的放松,却又像一张拉满的弓,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张力。
“买东西呢?”沈燃的嘴角勾起,是那种顾淮在酒吧里见过的、混合着嘲弄与了然的笑意。
顾淮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他试图从旁边绕过去。
沈燃却像预判了他的动作,不着痕迹地横移一步,再次挡在他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被拉近,顾淮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混合着阳光和某种植物皂角的干净气味,与那晚的烟酒味截然不同。
“我叫沈燃。”他主动报上名字,目光毫不避讳地在顾淮脸上逡巡,“燃烧的燃。你呢?”
顾淮不喜欢这种被审视的感觉,像一件待估的古董。他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平稳:“顾淮。”
“顾淮。”沈燃将这个名字含在嘴里,咀嚼了一下,仿佛在品尝它的味道。“哪个淮?”
“淮水的淮。”
“哦。”沈燃拖长了声音,点了点头,“好名字。听起来就……很安静。”
他说“安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于挑衅的玩味,仿佛这是一种需要被打破的缺陷。
顾淮不想再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对话。他抬起眼,目光第一次正式地、不带回避地迎向对方:“麻烦让一下。”
他的眼神很冷,这是他惯用的武器,是他用来与这个世界保持安全距离的屏障。以往,这招总是奏效。人们能读懂他目光里的“请勿靠近”,然后识趣地退开。
但沈燃显然不在这个“人们”的范畴里。他非但没有退开,反而又朝前逼近了半步。他忽然伸出手,快得让顾淮来不及反应。他的手指并没有触碰到顾淮的身体,而是在离他手腕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
一个悬停的、充满了暗示性的动作。
“你看起来,”沈燃的视线落在顾淮的手腕上,那里皮肤很薄,青色的血管在下面隐约可见,“不太健康。”
顾淮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的手腕是他自我规训的证明。稳定、有力,能用最精细的刻刀修复零点几毫米的榫卯结构。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这只看似平静的手下面藏着怎样失序的脉搏,尤其是在每一个被梦境惊扰的清晨。
沈燃的动作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医在“悬丝诊脉”,隔着虚空,却精准地探到了他最隐秘的病灶。
顾淮猛地后退一步,拉开了距离。一种被侵犯的感觉,远比任何实质性的触碰都来得强烈。
“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丝无法压抑的愠怒。
看到他这副反应,沈燃脸上的笑意反而更深了。他收回手,那副蓄势待发的姿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猫捉到老鼠后暂作休憩的慵懒。
“没什么,”他耸了耸肩,语气轻松得近乎残忍,“就是觉得你很有趣。不像这里的人,也不像来这里旅游的人。你身上有股味道。”
“什么味道?”顾淮下意识地问。
“枯木的味道。”沈燃说,“那种放在庙里,被人供奉了很久,外面看着好好的,里面其实已经空了的枯木。”
顾淮彻底僵住了。
如果说上一次的对视是挑衅,这一次的对话就是一场精准的、不留余地的剥皮。对方用一种近乎于直觉的野蛮,三言两语,就撕开了他用专业、用秩序、用冷漠包裹起来的全部伪装。
他看着眼前的沈燃,忽然觉得他不是飞蛾。飞蛾扑火,是奔向毁灭的同类。而这个人,他是火本身。他以燃烧他人为乐,以点燃那些看似不可燃的东西为趣。
顾淮没有再说话。他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柜台上,付了钱,然后一言不发地绕过沈燃,走出了杂货铺。
从头到尾,沈燃没有再阻拦他。
但顾淮能感觉到,那道灼人的视线像跗骨之蛆,一直黏在他的背后。直到他拐过街角,才终于消失。
回到住处,顾淮将买来的东西放在桌上,然后走到窗边机械地点燃了一支烟。他很少抽烟,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失控行为之一。尼古丁的苦涩迅速侵占味蕾,但他需要这种刺激,来对抗沈燃的言语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侵扰。
“枯木”。
他吐出一口白色的烟雾,看着它在潮湿的空气中慢慢消散。他想,他说得没错。
而现在,这截枯木,似乎遇到了火。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