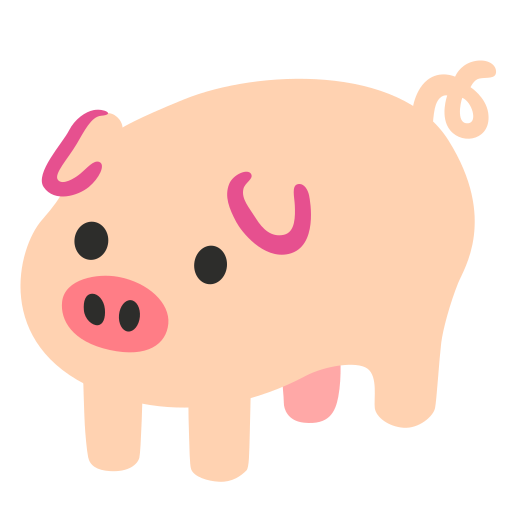2/ 飞蛾
编辑从城市去往那个名叫“云鹜镇”的地方,需要经历一场交通工具的逆向进化。飞机,高铁,然后是每日只有一班、沿着盘山公路颠簸行驶的绿色长途客车。当顾淮终于拎着他那只简洁的行李箱踏上小镇的土地时,感觉自己像一颗被吐出的果核,被现代文明彻底摒弃了。
空气的质感瞬间就变了。不再是城市里那种经过空调与空气净化器过滤后的中性气体,而是一种复杂的、有明确个性的混合物。潮湿的青苔,腐烂的落叶,不知名野花的幽香,以及一种从青石板路深处蒸腾起来的、属于古老时光的阴翳气息。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处于一种饱和到即将溢出的湿润状态。
镇子很小,一条主街,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木结构老屋。黑瓦,白墙,挂着褪色的红灯笼,像一幅年代久远的界画。张教授帮他提前联系好了住处,是镇上一户人家空出来的二楼,房东是一位沉默的老妇人,用一种混杂着方言的普通话交代了几句,便不再打扰他。
房间意外地干净,推开窗,能看到远方黛色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听雨亭就在那片群山深处。一种奇异的宁静笼罩着这里,但对顾淮而言,这种宁静反而像一块巨大的吸音棉,让他耳中关于梦境的回响变得愈发清晰。
最初的几天,他没有急着上山。他需要先让自己适应这里的“潮湿”,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白天,他研究项目资料,那些关于明代斗拱结构和楚式夯土技术的枯燥文字,是他对抗内心虚浮的锚。夜晚则变得格外漫长,失眠的症状并未因环境的改变而好转。他常常在后半夜独自出门,在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行走。
月光下的青石板泛着湿漉漉的光,像一条沉默的河。他走在上面,自己的脚步声是唯一的回答。他会走到镇子尽头的小桥上,听着桥下溪水不知疲倦的流淌。他想,这两千多年来,这水声或许从未改变。它听过楚人的悲歌,也听过明代工匠的号子。现在,它在听一个失眠者的心跳。
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他第一次见到了沈燃。
那晚他走得比平时更远一些,被一阵模糊的、充满颗粒感的音乐声所吸引。声音来自街角一栋建筑的二楼,那是一家看起来与整个小镇格格不入的酒吧。招牌上“飞蛾”两个霓虹字灯管坏了,缺了一笔,在夜色中闪烁得有些神经质。
顾淮从未涉足过这种地方。他生活里的声音,是打磨木料的砂纸声,是工具归位的金属碰撞声,是书籍翻页的细碎声。一切都精确,有序,在可控的分贝之内。而此刻从那扇窗户里泄露出来的,是另一种声音。它混乱、野蛮,充满了原始的冲击力,像一把钝刀,蛮不讲理地割开夜的静谧。
鬼使神差地,他推开了那扇门。
一股混杂着酒精、烟草和廉价香水的气味扑面而来。空间不大,光线昏暗,摇晃的彩色灯光像打翻的颜料,将每个人的脸都涂抹得不甚真切。一个临时搭起的小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奏。贝斯低沉的音浪撞击着他的胸口,让他感到一阵生理性的不适。
他找了个最不显眼的角落坐下,与周围狂热的氛围格格不入。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误入异教祭典的学者,冷眼旁观着一场他无法理解的仪式。然后,他看到了舞台中央的那个人。
那人握着贝斯,并不是主唱,但他身上散发出的光芒与能量,却让他在瞬间之内攫取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T恤,手臂上缠绕着大片的、在灯光下变幻着色彩的纹身。他的头发有些长,被汗水打湿,几缕贴在额角和颈侧,显出一种凌乱而危险的美感。
他弹奏贝斯的方式不像在演奏,更像在与乐器搏斗。手指修长,却带着一种凶狠的力量,在琴弦上跳跃、按压、撕扯。他的身体随着节奏剧烈地摆动,汗水从下颌滑落,在灯光下划出一道道晶亮的弧线。他微闭着眼,神情是全然的投入与沉醉,仿佛这个嘈杂的世界只剩下他与他手中的音乐。
那一刻,顾淮的呼吸停滞了。
他想起诗里写的句子:“西边的飞蛾探听夕照的虚实”。
如果说自己是一座被夕阳笼罩的、规则森严的空城,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是一只不顾一切扑火而来的飞蛾。他身上那种不管不顾的、燃烧般的生命力,正是顾淮所缺乏,甚至一直刻意压抑的东西。
一曲终了,爆发出的喝彩声与口哨声将顾淮拉回现实。舞台上的年轻人似乎耗尽了力气,他放下贝斯,拿起一瓶啤酒仰头灌下大半。喉结滚动,几滴酒液顺着脖颈没入汗湿的衣领。那是一个充满原始渴意的动作,带着毫不掩饰的性感。
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放下酒瓶,朝台下扫视。那双眼睛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明亮,像两簇小小的火苗。目光掠过一张张模糊而兴奋的脸,最终,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角落里的顾淮身上。
四目相对。
顾淮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对方的眼神里没有惊讶,而是充满了探究、挑衅,以及一丝与他年纪不符的、洞悉一切的了然。那目光太直接,太有侵略性,像手术刀,轻易就剖开了顾淮用冷静和疏离筑起的防线。
他看到那个年轻人咧开嘴,无声地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嘲弄,仿佛在说: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在这里?
顾淮无法形容那一刻的感觉。是狼狈,是冒犯,更是一种被窥破秘密的恐慌。他仓促地移开视线,站起身,近乎是落荒而逃般地离开了那家酒吧。
回到住处,他反锁上门,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出了一层薄汗。胸腔里的心跳依旧失序。酒吧里那股混杂的气味,那野蛮的音乐,以及最后那个充满挑衅的眼神,像无法删除的数据,在他脑中反复回放。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试图让夜风吹散那份烦躁。远山依旧沉默,月光依旧清冷。世界还是他所熟悉的那个样子。
但顾淮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个年轻人,那个像火焰一样的贝斯手,他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了他沉寂已久的梦湖。他不知道会泛起怎样的涟漪,但他有一种预感——平静结束了。
那个夜晚,他久违地没有做梦。他的失眠被另一种形式的清醒所取代。他睁着眼直到天亮,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是那双燃烧的眼睛,和那个无声的、嘲弄的笑容。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