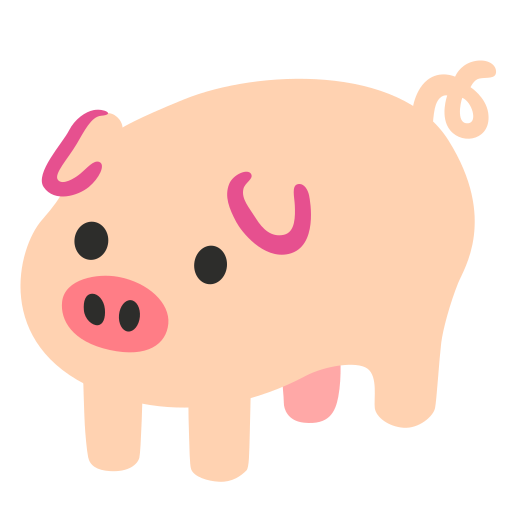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 枯木
编辑楚王梦雨
张枣
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
纷纷雨滴同享的一朵闲云
我的心儿要跳得同样迷乱
宫殿春叶般生,酒沫鱼样跃
让那个对饮的,也举落我的手
我的手扪脉,空亭吐纳云雾
我的梦正梦见另一个梦呢
枯木上的灵芝,水腰系上绢帛
西边的飞蛾探听夕照的虚实
它们刚辞别幽所,必定见过
那个一直轻呼我名字的人
那个可能鸣翔,也可能开落
给人佩玉,又叫人狐疑的空址
她的践约可能是澌澌潮湿的
真奇怪,雨滴还未发落的前夕
我已感到了周身潮湿呢
青翠的竹子可以拧出水
山谷来的风吹入它们的内心
而我的耳朵似乎飞入到了半空
或者是凝伫了而燃烧吧,燃烧那个
一直戏睡在里面,那湫隘(jiǎo ài)的人
还燃烧她的耳朵,烧成灰烟
绝不叫她偷听我心的饥饿
你看,这醉我的世界含满了酒
竹子也含了晨曦和岁月
它们萧萧的声音多痛,多痛
愈痛我愈要剥它,剥成七孔
那么我的病也是世界的痛
请你不要再聆听我了,莫名的人
我知道你在某处,隔风嬉戏
空白的梦中之梦,假的荷叶
令我彻夜难眠的住址
如果雨滴有你,火焰岂不是我
人神道殊,而殊途同归
我要,我要,爱上你神的热泪
雨是在顾淮醒来后才发落的。或者说,他是在梦境的最后一滴雨水中被现实打捞上岸的。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错觉,他早已无意纠正。
意识的浮力将他托举出睡眠的深海,周遭是卧房里熟悉的、近乎固执的干燥与寂静。没有雨声,只有中央空调送风系统如远方潮汐般单调的嗡鸣。顾淮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上那片由窗外城市余光所勾勒的毫无意义的几何图形。他的心跳平稳,呼吸均匀,像一台刚刚结束了精密运算的机器,正在冷却。
但那潮湿感依旧挥之不去。它并不附着于皮肤,而是更深,仿佛浸润了骨髓。一种属于梦境的、无孔不入的潮湿。
他坐起身,床头灯应声而亮,光线驱散了房间的暧昧,一切都还原为冷静的线条与色块。白墙,灰色床品,黑色的金属书架。这是一个被他本人精心编辑过的空间,剔除了所有不必要的叙事。就像他的人生。
床头柜上放着一杯隔夜水,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凉意顺着食道滑下去,短暂地压制了那股从内部蒸腾起来的湿气。
又是那个梦。
梦的场景从未变过:一座空旷的亭台,四面悬着竹帘,帘外是无尽的雨。他独自坐在亭中,面前一张斑驳的石案,上面总是温着一壶酒。他对面,隔着迷蒙的水汽坐着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人。那个人影,一个模糊的轮廓,会缓缓举起手中的酒杯朝他示意。像一种邀请,也像一种告别。他能感受到对方的目光,一种混杂着悲悯与戏谑的注视,穿透雨幕,落在他身上。他想开口问些什么,但喉咙里像被湿透的绢帛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甚至想看清对方的脸,但在每一次他试图这么做时,梦境便会像被稀释的水墨画,迅速褪色、溶解,最终只剩下那无休无止的雨声。
他就是在这雨声的渐弱中醒来。每一次。
顾淮起身走进浴室,镜子里映出一张轮廓清晰但略显疲惫的脸。二十八岁的年纪,时间尚未在他脸上刻下沟壑,只留下了一层淡淡的霜,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疏离感。他用冷水冲洗面孔,水流的触感短暂地覆盖了梦境的记忆。
他是顾淮,一名古建筑修复师。他的工作是与时间对话,将那些在岁月侵蚀下濒临溃散的木结构、瓦石、榫卯,从遗忘的边缘拉回来。这是一份需要极致耐心与精确性的工作,几乎等同于一种修行。他享受这种修行,享受将自己沉浸在木料的年轮、石材的肌理之中。在那些沉默的物质里,他能获得一种虚假但必要的永恒感。它们不会言语,不会擅自闯入他的边界,更不会像那个梦一样,带来扰人的潮湿。
早餐是永远不变的全麦面包和黑咖啡。他在平板电脑上浏览着当日的新闻,那些关于世界、关于他人的喧嚣,于他而言,不过是屏幕上滑动的像素矩阵。直到一封新邮件的提示弹出。
发件人是“江南古典园林研究会”的张教授,一位与他有过数次合作的学者。邮件内容言简意赅,附件里是一个新项目的资料。
他点开附件,指尖在屏幕上滑动。项目地点:湘西,一座至今尚未完全开发的深山。项目主体:一座建于明代中期的园林“听雨亭”,据地方史志考证,其选址位于一座晚楚时期行宫的遗址之上。
“听雨亭”。
顾淮的指尖停住了。
他将这三个字在唇齿间无声地咀嚼,一种奇异的、近乎于金属质地的回甘在舌根泛开。这是一种宿命般的巧合,巧合得近乎粗暴,让他无法回避。
他继续往下看。资料阐述得更为清晰:这座明代的亭子本身已是珍贵的文物,但数月前的一场山体滑坡,不仅严重损毁了亭子的侧翼,更意外地将亭下深埋的土层冲开,暴露出了属于更早年代的、疑似战国晚期楚式风格的夯土台基和几枚零散的青铜构件。这个发现让整个项目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一次单纯的古建筑修复,而是一场修复与考古并行的复杂工作。
顾淮放大了一张现场勘测的照片。照片上,明代亭子那残破的飞檐从泥土与乱石中顽强地伸出来,像一只折断的鸟翼。而在它坍塌的基座下方,可以清晰地看到颜色更深、质地更紧密的夯土层,以及考古队插上的白色标记签。镜头被雨水打湿了,画面有些模糊,但这恰好赋予了现场一种时间交叠、新伤与旧魂纠缠的挣扎感。
那股熟悉的潮湿感,隔着屏幕,再一次漫了上来。
他想起了自己的工作台。那些等待被修复的古代木料,它们躺在那里,沉默而驯服。他熟悉它们的每一寸纹理,熟悉它们因年代久远而发出的、混合着尘土与树脂的微香。他总能将它们复原,让榫卯重新严丝合缝,让梁柱再次支撑起一片屋檐。他像一个外科医生,冷静地解剖、清创、缝合,赋予那些濒死的“枯木”第二次生命。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那个赋予生命的人。
可现在,看着照片里那座明亭的残骸与楚墓的地基,他第一次有了一种被召唤的错觉。历史在这里形成了断裂,又因一场灾难而强行缝合。上层的建筑是他所熟悉的“枯木”,而下层的遗址,则是寄生于枯木根系的、更古老的灵芝。一个致命的诱惑,一个不知通往何处的谜题。
张教授在邮件末尾写道:小顾,这个项目难度很高,环境也艰苦。既要修复明代建筑,又要配合考古队对楚时遗址进行勘测评估,需要极强的专业性和全局观。我们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你。希望你能考虑。
顾淮关掉邮件,端起已经冷透的咖啡。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时阴沉了下来,城市的轮廓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有些不真实。他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那个倒影也在看着他。
他的人生是一座被精心维护的空亭,他用工作、用秩序、用沉默,将自己牢牢地关在里面。他以为这样很安全。
但那个梦,如亭外的雨,总会准时到来。它在呼唤他,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
或许,是时候走出去了。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走近。走进那场雨里,去看看是明朝的工匠,还是楚国的君王,留下了他梦中的回响。去看看那个一直对他举杯的人,究竟是谁。
他重新打开邮件,光标在空白的回复框里安静地闪烁。他伸出手指,用一种近乎于按下命运开关的郑重,敲下了两个字。
“我去。”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