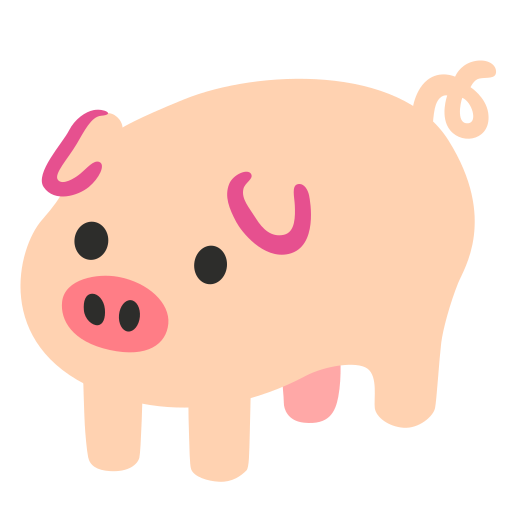7/ 花落
编辑江南古镇的修复项目,在初冬的第一场寒流抵达时正式竣工。
剪彩仪式办得很隆重。江越作为投资方站在镁光灯的中央,言辞得体,滴水不漏。顾念则安静地站在人群的边缘,像个与这场热闹无关的局外人。他们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彼此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一如初见时那场酒会,仿佛中间这段时间的波澜,都只是一场无人知晓的幻觉。
项目结束,也意味着他们之间最后一条业务上的纽带,就此断开。
仪式结束后,江越没有参加庆功宴。他在那座被修复如初的古寺里找到了顾念。顾念正独自一人,站在主殿那根被他亲手加固过的金丝楠木主梁下,仰头看着穹顶那重焕光彩的藻井,神情专注。
“很美。”江越走到他身边,轻声说。
“嗯,”顾念应道,“再过一百年,它应该还会在。”
“一百年……”江越咀嚼着这个词,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怅然,“我们都成灰了。”
两人陷入了沉默。夕阳的余晖透过格扇窗,在被打磨得光滑如镜的金砖地面上,投下两道被拉得极长的、孤独的影子。
“我下周要去苏黎世。”江越忽然开口,打破了这份宁静,“有一个新的项目,可能会待很久。”
顾念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攥了一下,不疼,却是一种缓慢下沉的、空落落的感觉。他侧过头,看着江越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边的侧脸。“是吗?那很好。”
“你……”江越似乎想问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最终只是笑了笑,说:“以后,可能就没机会来你工作室蹭茶喝了。”
那语气,像是在为一段漫长的、无果的旅途画上一个礼貌而体面的句号。
顾念没有挽留,也没有追问。他只是说:“那里的冬天很冷,多带些衣服。”
他们告别,就在这座被他们联手赋予了新生的古寺里。没有拥抱,没有承诺,甚至没有一句“多保重”。像两个最默契的棋手,在棋局终了时,各自收子,起身,静默离场。
江越离开的那天,寒流抵达了顶峰。
一夜之间,气温骤降。南山上的那些梅树,仿佛接收到了某种决绝的指令,蓄积了一整年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尽数盛开。然后在那同样酷烈的寒风中,又纷纷扬扬地开始飘落。
顾念独自一人待在他的工作室里。他没有开灯,巨大的落地窗将那场漫山遍野四处飘落的梅花尽数映入室内,为这安静的空间铺上了一层流动的、凄美的微光。
他的脚边,散落着古镇项目的最后几张设计图纸,白色的纸张,如同提前落下的花瓣。
他坐回了那个江越常坐的位置,那个他自己也常坐的位置。他给自己泡了一壶茶,然后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看着那场覆盖了整座南山的、沉默的告别。
他想,江越或许正在几万英尺的高空,飞往一个全新的未来。而自己,也将继续守着这些不会说话的梁木与砖石,度过又一个平静无波的十年。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也许,此生都不会再见了。
后悔吗?
顾念在心里问自己。
如果当年,江越选择的是反抗,而不是妥协;如果自己,能更勇敢一些,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结局。如果……
他想起了大学的游泳馆,那个少年矫健的身姿。想起了废弃的瞭望塔,那在风中呼喊他名字的、无所畏惧的声音。想起了那个雨夜的车里,那张滚烫而沾满泪水的面颊。
所有这些记忆,无论痛苦还是甜蜜,此刻都像窗外那些飞舞的花瓣,在他的脑海里盘旋,落下。
他慢慢地端起茶杯,杯中的茶水,映着窗外漫天的花雨。
“后悔吗?……也许吧。”
他看着那场似乎永远不会停歇的落梅,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也对着自己的内心,轻声说道:
“但你看,也很美。”
是的,很美。
那些无法挽回的过去,那些被记忆反复美化的悔憾,那些在时间长河中错失的爱意与温柔,最终都化作了眼前这场落满了整座南山的梅花和雪。
它覆盖了一切,也成就了一切。就像二人这段感情,连同它所有的危险、美丽、羞惭与伤痛,已经化为了一片永恒的、只属于他一个人的风景。
茶气氤氲,窗外的梅花还在飘落。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