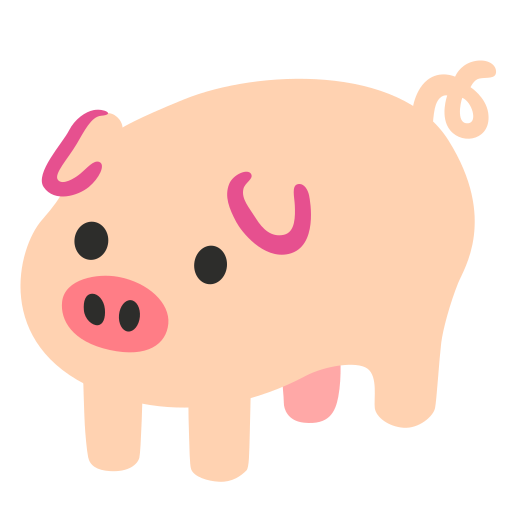6/ 潮湿
编辑自那天下午不欢而散的拜访之后,某种危险的平衡被打破了。顾淮和沈燃像两颗轨道偏离的行星,开始不可避免地加速靠近。
他们之间不再有刻意的回避或试探。沈燃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工地上,不说话,只是找个角落坐下,看着顾淮工作。他的目光是一种沉默的、持续的在场,像无形的压力,让顾淮无法忽视。而顾淮也默许了这种侵入。他甚至会在下山时,习惯性地在暮色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们很少交谈,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存。仿佛语言是多余的,他们通过空气中震动的频率就能感知彼此的存在。
这种沉默的共存在某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抵达了临界点。
那晚的雨比上一次更大,更凶猛。豆大的雨点疯狂地砸在工棚的铁皮屋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仿佛要把这个脆弱的人造物彻底摧毁。修复工作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瓶颈,一块关键的承重木料因为内部的腐朽超出了预期,导致整个修复方案必须推倒重来。
团队的所有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难题搅得心烦意乱,早早便下山了。顾淮独自一人留在工棚里,对着一堆失效的数据和图纸,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他的世界建立在精准的计算和严密的逻辑之上,而此刻,这套体系失灵了。他像一个迷航的船长,失去了所有的星图和罗盘。
雨声,梦境,沈燃的存在,工作的困境——所有失序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将他牢牢困住。
就在这时,工棚的门被推开了。裹挟着一身风雨的沈燃走了进来。他浑身湿透,头发上的水珠顺着脸颊滚落,T恤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结实起伏的身体线条。他像是刚从深海里走出来,带着一股原始而野性的潮气。
“我就知道你还在这儿。”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声音因雨声的衬托而显得格外清晰。
顾淮没有抬头,他只是盯着桌上那张废弃的图纸,图纸被窗缝渗进的雨水打湿了一角,蓝色的线条晕染开来,像一幅失败的抽象画。
“滚出去。”他说,声音很低,带着压抑到极致的疲惫和怒火。
沈燃没有滚。他走到顾淮面前,拿起桌上那叠厚厚的计算稿,看了一眼,然后随手扔在一边。“这些东西救不了那块烂木头。”他说。
“你懂什么?”顾淮终于抬起头,眼中布满了血丝。这是他第一次将自己最狼狈、最失控的一面暴露在另一个人面前。
“我不懂,”沈燃直视着他的眼睛,目光灼灼,“但我知道,你快把自己逼死了。你看起来就像这块烂木头一样。”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顾淮紧绷的神经。他猛地站起身,胸膛剧烈地起伏,所有的理智在这一刻都断了线。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或许是想把眼前这个人推出去,或许只是想做点什么来发泄这股无处可去的狂躁。
他抓住了沈燃的衣领。
沈燃没有反抗。他任由顾淮抓着,身体微微前倾,两人之间的距离被缩短到极致。顾淮能闻到他身上雨水的腥甜和皮肤本身散发出的、温热的气息。他能看到对方眼中自己的倒影——一个因为愤怒而面容扭曲的、陌生的自己。
“你到底想怎么样?”顾淮的声音沙哑,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沈燃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了平日的戏谑和挑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得近乎悲伤的情绪。他缓缓抬起手,覆在顾淮抓着他衣领的手背上。他的手心滚烫,与顾淮冰冷的手背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想怎么样?”他轻声反问,像一声叹息,“顾淮,是你……想怎么样?”
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顾淮内心最深处的闸门。被压抑的欲望、孤独、对梦境的恐惧和沉迷,在这一刻,如洪水般倾泻而出。
他松开了沈燃的衣领,但并未后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粗暴的、近乎于啃咬的吻。
这个吻充满了愤怒和绝望,没有任何温柔可言。是两头困兽在黑暗中的相互撕扯,企图在对方身上寻找一个出口。雨声是他们唯一的背景音乐,激烈、狂暴,应和着室内同样失控的一切。
沈燃起初有些错愕,但随即,他反客为主,用一种更具侵略性的姿态回应着。他扣住顾淮的后脑,将这个吻加深。这不是一场情欲的交流,而是一场权力的交接。顾淮发起了这场战争,却在瞬间之内,就彻底沦陷。
他们从桌边纠缠到墙角,撞翻了椅子,图纸散落一地。汗水,雨水,呼吸,喘息,混合在这间狭小的工棚里,空气变得粘稠而滚烫。
在某个混乱的间隙,顾淮被推倒在一张临时搭起的行军床上。沈燃的身体覆了上来,带着不容抗拒的重量和热度。他撕开了顾淮被汗水浸湿的衬衫,纽扣崩落,发出细碎的声响。
“看着我。”沈燃的声音响在顾淮耳边,沙哑而专横。
顾淮被迫睁开眼。
越过沈燃汗湿的、起伏的肩膀,他看到了窗外。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照亮了雨中的听雨亭。那残破的飞檐,在那一刹那竟显出一种诡异而完整的美。
然后,黑暗重新降临。
他感觉到自己被进入了。一种撕裂般的痛楚,伴随着一种被填满的、奇异的满足感。他抓紧了身下的床单,指甲几乎要嵌进帆布里。他没有喊叫,只是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压抑的、近乎于呜咽的闷哼。
沈燃的动作是凶狠的,带着惩罚和占有的意味。他像一个高明的工匠,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强行地、一寸寸地,楔入顾淮的身体,修复着他内在的空洞。
顾淮放弃了抵抗。
在这极致的痛苦与极致的快感中,他的意识开始剥离。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梦里,他就是那座宫殿春夜里的空亭,而沈燃,是那场无休无止的、潮湿的雨。雨水穿过他所有的缝隙,冲刷着他每一寸干枯的结构。
他不是在被侵犯。 他是在被一场大雨,彻底地、不留余地地,浸透。
?别看
他松开了手,却用一个更凶狠的动作堵住了所有的话语。
那不是一个吻。那是一场关于边界的战争。他尝到了雨水的味道,和一丝属于沈燃的、像铁锈般的咸涩。外界的暴雨声仿佛在瞬间被吸入了他们的身体内部,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雷鸣的回响。
世界倾斜了。
他感觉不到桌椅,也感觉不到墙壁。他只感觉到自己成了一座空置已久的建筑,在狂风暴雨中发出痛苦的呻吟。而沈燃,是这场风暴本身。他听见那些干枯的、常年紧绷的榫卯结构,在一股蛮横的外力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断裂前的“咯吱”声。
痛楚是尖锐的,像一根滚烫的金属探针,毫无征兆地刺入了最核心、最脆弱的结构里,探寻着空洞的根源。他下意识地挣扎,却被更强大的力量所禁锢。那力量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入侵与占据。
然后,那道防线,那道他用理智和秩序筑起的、抵御了二十八年人生的防线,彻底崩塌了。
痛楚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强行灌溉的、令人战栗的饱和感。那座徒有其表的空亭变成了洼地。所有的雨水,都朝着他奔涌而来。他听见水流冲刷过干燥地面的声音,看见干涸的裂缝被一一填满,看见枯死的根系被迫重新吸吮水分。
闪电划破夜空,光亮透过窗户,在他紧闭的眼睑上留下一道惨白的残影。在那一刹那,他看到的不是工棚,而是那座梦中的亭台。四面竹帘被狂风吹起,亭外的雨,第一次,泼了进来。
他抓紧了身下的某处粗糙的平面,指甲深陷,仿佛那是他在这场颠覆中唯一能抓住的现实。他张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急促的、破碎的喘息。他感觉自己正在被瓦解,又在被重塑。每一寸结构都在这潮湿的入侵中被重新定义。
顾淮明白,他正在被一场大雨,彻底地、不留余地地,浸透。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