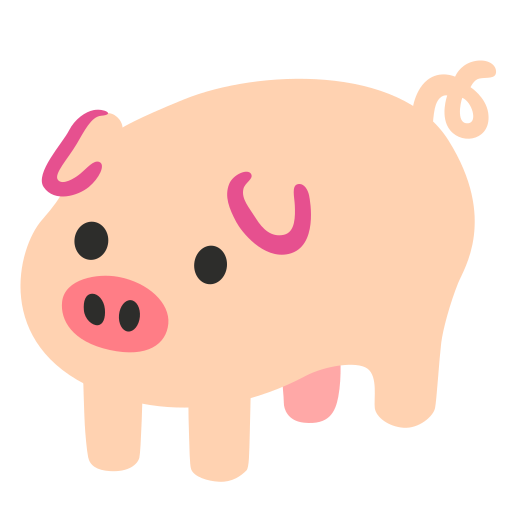2/ 废墟 余温
编辑那次巷口的相遇,像一颗投入李怀今平静生活里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久久未散。他开始在学校里下意识地寻找陈东的身影。他们虽然同级,却分属两个世界——李怀今在一班,教室在教学楼采光最好的南面;陈东在七班,在楼层另一头的角落里。
但学校总有公共的时刻。比如每天课间操的时候,李怀今站在自己班级的整齐队列里,目光总会越过人群,投向操场后方七班凌乱的队伍。陈东总是站在队伍的最后,姿势懒散,对领操台上的口令置若罔闻。他常常和身边几个同样无所谓的男生说笑,或者干脆靠着后面的篮球架,阳光照在他身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整个人都带着一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疏离感。
有时在走廊里,李怀今也会碰到他。陈东通常都是一个人走,或者被教导主任拦在办公室门口训话,他总是那副不耐烦却又沉默的样子,下巴微微扬着,像一头桀骜不驯的豹子。每当这时,李怀今都会装作不经意地走过,心脏却擂鼓般地跳动。
放学后,那道沉默的身影成了他回家的固定背景。陈东从不靠近,也从不搭话,总是隔着三五十米的距离,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守护,带着一种近乎蛮横的温柔。李怀今不再害怕那些巷子,甚至开始有些期待走过那段路。被那样一双眼睛注视着,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包裹起来的安全感。
一个星期后,李怀今又在校门口看到了陈东。他靠在墙上,嘴角有一块明显的青紫,眼角也破了皮,渗着血丝。他面无表情地抽着烟,姿态像一头舔舐伤口的年轻野兽。李怀今的心被那块刺眼的伤口揪了一下,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攥着书包带走了过去。
他从书包里翻出一小包碘伏棉签和一张创可贴,那是母亲硬塞给他备用的。他把东西递到陈东面前,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你……擦一下吧。”
陈东的目光从他的头顶落到他递过来的东西上,沉默了几秒。他没有接,而是掐灭了烟,用没受伤的那边嘴角勾起一个极淡的弧度,说:“没事。”
“会感染的。”李怀今坚持着,又把手往前递了递。他的指尖因为紧张而有些冰凉。
陈东看了他一会儿,终于伸出手,却不是去接那包棉签,而是直接抓住了李怀今的手腕。他的手掌干燥而粗糙,带着惊人的热度,瞬间将李怀今手腕的皮肤烫得一片滚烫。李怀今像触电一样想缩回手,却被他牢牢钳住。
“跟我来。”陈东不容置疑地说完,拉着他就朝工厂的方向走去。
他们穿过铁轨,绕过一排废弃的仓库,来到工厂最东边的围墙下。这里有一个不起眼的缺口,陈东熟门熟路地钻了进去。这里是钢厂的边缘地带,堆放着生锈的钢材和废弃的零件,像一座钢铁的坟场。陈东领着他爬上一个早已停止使用的露天货运平台的旋梯。
旋梯又高又陡,铁皮在脚下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李怀今有些恐高,但他被陈东拉着,只能一步步向上。到了平台顶端,视野豁然开朗。
整个钢城尽收眼底。无数灰色的屋顶像鱼鳞一样铺展开,远处高炉和烟囱组成的钢铁森林直指天际,正吐出灰白的、疲惫的烟。一条铁锈色的河流沉默地穿城而过。从这个高度看下去,平日里觉得压抑而巨大的工厂,此刻竟有了一种悲壮而荒凉的美感。
“这是我的地方。”陈东松开手,淡淡地说。
风很大,吹得李怀今的校服外套猎猎作响。他走到平台边缘,冰冷的铁栏杆让他感到一阵眩晕。陈东在他身边坐下,双腿悬在半空中,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然后才接过李怀今手里的碘伏棉签,随意地在嘴角的伤口上抹了抹,疼得他“嘶”了一声,眉头却没皱一下。
李怀今在他身边坐下,学着他的样子也把腿伸出平台。脚下是几十米高的虚空,一种危险的刺激感让他心跳加速。
“你怎么又打架了?”他小声问。
“看人不顺眼。”陈东的回答简单粗暴,吐出一口烟圈,烟雾瞬间被风吹散。
李怀今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两人陷入了沉默。只有风声和远处工厂传来的、沉闷的机器运转声。过了一会儿,李怀今从书包里拿出他的松下牌Walkman,分了一只耳机给陈东。
“听吗?”
陈东看了他一眼,接了过来,塞进耳朵里。李怀今按下了播放键,磁带转动,一阵失真而狂躁的吉他riff瞬间灌入耳膜。是Nirvana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科特·柯本那如同嘶吼般的嗓音,充满了愤怒、迷惘和彻底的破碎感,与这片衰败的工业景象形成了奇妙的共鸣。
陈东显然从未听过这种音乐,他愣住了,身体微微前倾,似乎想听得更清楚一些。李怀今靠过去,把自己的那只耳机也塞给了他。为了让两边都能戴上,他们的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
李怀今能闻到陈东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一种肥皂的气息,还能感觉到他呼吸时带出的热气,轻轻拂过自己的耳朵。他的心跳又开始失控。整个世界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和耳机里那个绝望的嘶吼声。一首歌放完,陈东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Walkman,示意他倒回去再放一遍。
那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高台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一盘磁带。
从那以后,那个废弃的平台就成了他们的秘密据地。李怀今会带去新的磁带和书籍,而陈东则会像变戏法一样,从某个角落摸出两个烤得滚烫的红薯,或是一捧炒得喷香的瓜子。
他们开始有了真正的交谈。李怀今给他讲书里的故事,讲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讲余华笔下的苦难。陈东则教他分辨远处不同车间的机器声音,告诉他哪座烟囱的烟变得稀薄,就意味着那个分厂的活儿快没了。
李怀今这才知道,陈东的父亲是厂里最好的炼钢工之一,凭着肉眼就能判断钢水的温度,但前阵子在一次事故中伤了腰,干不了重活了,人也变得消沉。他还知道,陈东那条微跛的腿,是小时候在铁轨上玩,为了救一个差点被火车撞到的小孩而落下的。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让陈东的形象在李怀今心中变得立体而真实。他不再只是一个会打架的“问题学生”,他是一本更厚重、更难懂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这个城市投下的、粗粝的阴影。
一天傍晚,他们又坐在平台上。夕阳正沉入地平线,把天空和浓烟都染成了瑰丽的紫红色。工厂的汽笛破天荒地没有在五点钟准时响起。
“听见没?”陈东忽然说。
“听见什么?”
“什么都没听见。”陈东的目光投向远处那片沉默的钢铁森林,“换班的汽笛没响。三车间今天停产了。”
李怀今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他想起最近父亲回家后越来越少的笑容和越来越长的叹息,想起饭桌上母亲小心翼翼提起“减员增效”时父亲那难看的脸色。一股巨大的、无形的阴影,正缓缓地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他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就像温水里的青蛙,直到此刻才清晰地感觉到水温正在增长。
李怀今转头看着陈东的侧脸,夕阳的余晖勾勒出他坚毅的轮廓。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或许即将崩坏,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但在他身边,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废墟之上,他却感到了一丝真实的、微小的温暖。
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陈东的手背。陈东的手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粗糙,但很暖。
陈东身体僵了一下,回过头看他。他的眼神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深邃,像一片藏着风暴的海。
李怀今没有缩回手。那一刻,他什么都没想,只是本能地想抓住这点温暖。在巨大的、冰冷的钢铁废墟的环绕下,两个少年的体温,成了对抗整个世界寒意的唯一证据。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