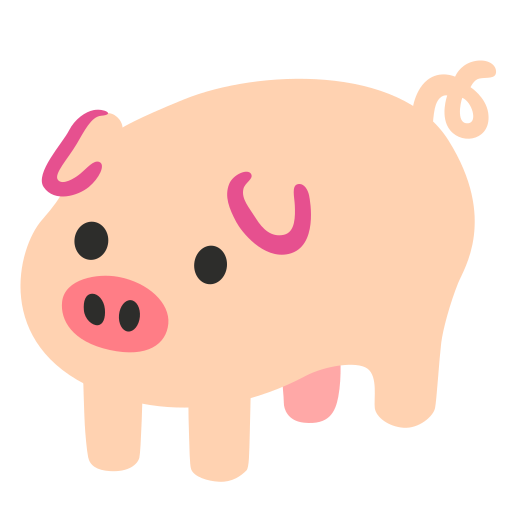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 霜雪 初逢
编辑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早,也更决绝。才刚十一月,西伯利亚的寒流就毫不客气地越过山岭,像一头无形的巨兽,将这座名叫“钢城”的东北重工业城市一口吞下。天是铅灰色的,被工厂烟囱吐出的浓烟搅得浑浊不堪,太阳像一枚被磨花了的镍币,无力地挂在天上,吝于施舍任何温度。
李怀今放学回家的路,必须穿过一条夹在两栋旧式“筒子楼”之间的巷子。风在这里会变窄,加速,发出呜呜的、像哭一样的声音。他拉高了外套的拉链,试图把下巴也缩进去,但那风还是能找到缝隙,像冰冷的刀片一样割着他的皮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味,是燃烧不充分的蜂窝煤、劣质油漆和隐约的酸菜味儿混合在一起,这是钢城冬天的味道,也是李怀今从小闻到大的味道。
他怀里紧紧抱着一本《百年孤独》,书页被冻得有些发硬。这是他从市里唯一那家新华书店淘来的,花了他积攒两个月的零花钱。对于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马孔多的潮湿雨林,吉普赛人的神奇发明,以及布恩迪亚家族那纠缠百年的命运,是他抵御身边这个坚硬、冰冷世界的壁垒。
巷子尽头,三个身影堵住了去路。
李怀今的心猛地一沉。是三中的那几个职高生,为首的叫赵磊,剃着青皮,耳朵上挂着个银晃晃的铁环,总在他们这些重点高中的学生放学路上晃荡。他认得李怀今,也认得李怀今身上那件还算簇新的校服,更认得他那副一看就没挨过揍的样子。
“哟,这不是钢厂总工的公子吗?”赵磊的语调拖得长长的,带着嘲弄。他身边两个跟班笑起来,哈出的白气在空中散开。
李怀今捏紧了怀里的书,没说话,只想从旁边绕过去。
“急着走啊?”赵磊一步横在他面前,伸出手,“天冷,哥几个手头紧,借点钱买包烟抽抽,暖和暖和。”
“我没钱。”李怀今的声音有些发干。
“没钱?”赵磊夸张地掏了掏耳朵,“总工程师的儿子说自己没钱?你糊弄鬼呢?”他一把抓向李怀今的衣领。
李怀今本能地后退,却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踉跄着撞在布满冰霜的墙壁上。《百年孤独》从他怀里滑落,“啪”的一声掉在肮脏的雪地上。
这一声比打在他身上还让他难受。他想弯腰去捡,赵磊却一脚踩在了书的封面上,还恶意地碾了碾。“什么破玩意儿?”
“你别动它!”李怀今急了,第一次鼓起勇气抬头瞪着赵磊。那眼神里没有多少威慑力,更多的是一种被侵犯了领地的屈辱。
赵磊似乎很享受这种眼神,他笑得更开心了:“嘿,还敢瞪我?今天不光钱要留下,人也得给哥几个练练手。”
就在赵磊扬起拳头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巷子口传来,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投进冰湖,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
“你们干什么呢?”
所有人都循声望去。
巷口站着一个少年,和他们年纪相仿,穿着和李怀今同款、但洗得发白且明显短了一截的校服。他个子不算特别高大,但身形很挺拔,像一杆扎在雪地里的标枪。他的脸部轮廓很深,鼻梁高挺,嘴唇很薄,此刻正抿成一条没什么感情的线。最让人无法忽视的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黑沉沉的眸子,在铅灰色的天光下,像两点凝固的、没有温度的墨。
是陈东。
钢城一中无人不知的名字。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打架。据说他一个人能放倒三个,也据说他被学校记过处分,差点开除。他是另一个世界的物种,是这片锈迹斑斑的工业区里野蛮生长出的荆棘。
赵磊显然也认识他,脸上的嚣张收敛了些许,但依旧嘴硬:“我当是谁,原来是陈东啊。怎么,想管闲事?”
陈东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越过赵磊,落在了李怀今身上,又缓缓移到那本被踩在脚下的书上。他什么都没说,但李怀今却从他那毫无波澜的眼神里,读出了一丝极淡的、类似“原来是你”的意味。他们在同一个年级,但从未有过交集。李怀今是老师口中的骄傲,陈东是他们谈论时的叹息。
陈东这才把目光转回赵磊脸上,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步伐很稳,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每一步都像踩在人的心跳上。
“把他放了。”他说,是陈述句,不是商量。
“凭什么?”赵磊色厉内荏。
陈东没再废话。他的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欺身而上,右手抓住赵磊扬起的那只手腕,向下一折,同时左手手肘精准地撞在赵磊的肋下。
一声闷哼。赵磊的身体像煮熟的虾一样弓了起来,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那两个跟班想上来帮忙,却被陈东回过头的一个眼神钉在了原地。那眼神里有一种近乎凶残的平静,让他们毫不怀疑,如果自己再上前一步,下场会比赵磊惨得多。
整个过程不到五秒钟,没有多余的动作,干净利落得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陈东松开手,赵磊软软地滑到墙角,捂着肚子干呕。
“滚。”陈东只说了一个字。
那两人扶起赵磊,连句狠话都没敢放,屁滚尿流地消失在巷子深处。
世界重新安静下来,只剩下风声和李怀今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陈东弯下腰,捡起了那本《百年孤独》,拍了拍上面肮脏的脚印,封面已经留下了一道无法磨灭的污痕。他把书递给李怀今。
李怀今伸手去接,指尖不小心碰到了陈东的手。陈东的手很冷,像铁,但更让他心惊的是那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和指关节上新旧交错的伤疤。那是一只打过无数次架、也干过无数粗活的手。
“谢谢。”李怀今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
陈东没应声,只是看着他。他的目光很有穿透力,看得李怀今有些不自在,仿佛自己那些被小心隐藏起来的敏感和脆弱,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
“住钢厂大院的?”陈东忽然开口,嗓音有些沙哑。
李怀今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几号楼?”
“三号……总工楼。”他说出最后三个字时,声音更小了。在钢厂这个等级分明的小社会里,“总工楼”三个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阶级和距离。
陈东听完,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那双黑沉沉的眸子似乎又深了一些。他转过身,朝巷子另一头走去。
李怀今以为他就要这么走了,连忙跟上两步,说:“我……我叫李怀今。”
陈东的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李怀今不知道该再说什么,只能抱着书,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几米远的地方。陈东走得不快,李怀今这才发现他的一条腿似乎有点轻微的跛,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看着陈东的背影,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绷紧在他宽阔的肩胛骨上,勾勒出少年人富有力量感的轮廓。他像一头习惯了独行的狼,沉默地走在自己的领地里,周身都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息。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刚才却救了他。
两人一前一后,沉默地走着。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雪粒落在他们头发上、肩膀上。李怀今能看到陈东的后颈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和他黝黑的皮肤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来,他想走上前,替他拂去那点雪。
这个念头让李怀今自己的脸先烫了起来。
到了大院门口,前面出现了岔路。左边是厂领导和高级工程师们住的红砖小楼,干净整洁。右边是普通工人住的筒子楼,拥挤而嘈杂。
陈东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右边。在岔路口,他停下脚步,终于回头看了李怀今一眼。
天色更暗了,远处巨大的冷却塔像沉默的巨人一样矗立在暮色中。陈东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模糊,只有那双眼睛依旧明亮。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朝李怀今家的方向抬了抬下巴,然后就转身,走进了右边那条通往烟火与嘈杂的路上。
李怀今站在原地,看着陈东的背影消失在一栋筒子楼的门洞里,那黑暗像一张巨口,瞬间就将他吞没了。
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书,那个黑色的脚印丑陋地印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画像上。他伸出手指,轻轻地、徒劳地摩挲着那个印记。
寒风愈加刺骨。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