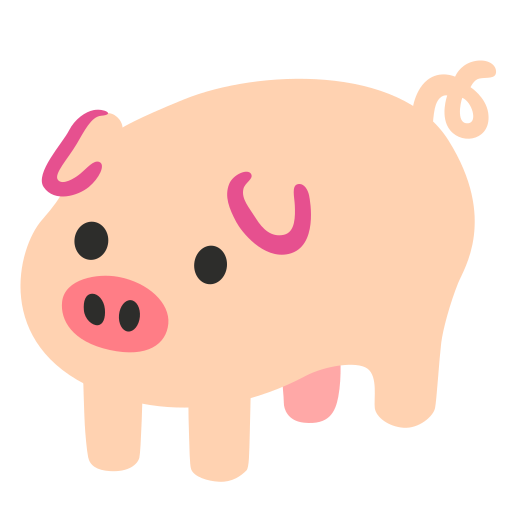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4/ 歧路 江湖
编辑李怀今在象牙塔里感受着精英教育与精神孤独的拉扯时,陈东正在南国的泥沼里,被生活逼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布满荆棘的道路。
五金厂的生涯,在第二年夏天的一个电话后,戛然而止。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她在那头泣不成声。父亲,那个也曾在陈东面前顶天立地的男人,在长期的酗酒和抑郁中彻底垮了。严重的肝硬化加上并发的胃出血让他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后续的治疗和休养需要一大笔钱。
挂掉电话,陈东在那间嘈杂的公共电话亭里听着自己胸腔里擂鼓般的心跳。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仅仅是按月寄钱,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懦弱逃避。钱可以治父亲的病,但治不了他的心。只要他们还生活在那个充满了流言蜚语和失败记忆的环境里,父亲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好起来。
一个念头像子弹瞬间击中了他:必须带他们走。
离开那片冰冷的、正在沉沦的土地,来这个虽然残酷、却充满生机的南方。这成了他心中一个疯狂而坚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在工厂里靠苦力,一辈子都不可能。
他想到了在老乡聚会上认识的彪哥。
彪哥不是本地人,也是从北方下来闯荡的,靠着一股狠劲和精明拉起了一支队伍,做着物流和安保的灰色生意。
陈东主动找上了门。
彪哥起初并没把他这个半大的小子放在眼里,但当陈东沉默地、面无表情地替他挡下了一个闹事酒鬼砸过来的酒瓶,并且在额头鲜血直流的情况下,眼神都没有丝毫变化时,彪哥知道,他捡到宝了。
陈东就这样离开了那间挥洒了两年汗水的五金厂,一脚踏入了“江湖”。
他从最底层的马仔做起,跟着彪哥的车队送货、收款、处理纠纷。这个世界比工厂更复杂,也更危险。这里不看文凭,不看背景,只认实力和义气。陈东话不多,但做事稳,下手狠,而且脑子清楚。他很快就发现,物流的线路、市场的摊位、人际的纠葛,里面都有着可以攫取利益的缝隙。
一次,两个市场的地头蛇因为抢生意起了冲突,眼看就要火并。彪哥正头疼时,陈东却独自一人找到了对方的老大,他没带刀,只带了一包烟和一本账。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冷静地给对方分析了火并的损失和合作的利润。他的分析有理有据,又带着一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狠劲。最终,一场可能见血的冲突被他用一种近乎商业谈判的方式化解了。
这件事让他在整个市场里一战成名。彪哥对他刮目相看,开始将一些核心的业务交给他打理。
陈东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搬出了拥挤的宿舍,有了自己的单间。他不再需要为一日三餐发愁,甚至能穿上体面的衣服。他寄回家的钱,也从几百块,变成了几千块。父亲的病情因为有了及时的医药费,总算稳定了下来。
他成了别人口中那个“混出头了”的“东哥”。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正在离那个记忆中的少年越来越远。他的手上开始沾染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像那些他曾经最瞧不起的成年人。他学会了在酒桌上与人虚与委蛇,也学会了在暗巷里用最有效的方式让对手闭嘴。
他像一条在黑暗水域里潜行的鱼,为了生存,长出了坚硬的鳞片和锋利的牙齿。
李怀今的存在,成了他内心深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禁区。
他从母亲的家信里,得知李怀今考上了上海的名牌大学,也知道了李怀今家里为了他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过得也并不宽裕。李振宏的总工职位在工厂改制后变得有名无实,工资也大不如前,还因为理念不合成了新管理层的“眼中钉”,被逼得马上要离开岗位。
在一个深夜,陈东从一个KTV的酒局里脱身,带着满身的酒气,去银行将一笔不小的钱汇入了母亲的账户。他在附言里,用只有他们母子才懂的暗语写道:“给家里还人情。”
几天后,母亲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他,她把那笔钱,以“厂里补发下岗工友困难补助”的名义,托一个可靠的老邻居悄悄送给了李怀今的母亲。李家推辞了很久,但最终因为实在困难,还是收下了。母亲在电话里感叹:“也算是还了当年李总工没把事情做绝的情分了。”
陈东“嗯”了一声,挂掉了电话。
他用自己挣来的、也许并不干净的钱,供养着那个在他心中永远干净的少年去追求一个光明而坦荡的未来。这是一种隐秘的、带着赎罪意味的守护。他像一个最卑微的信徒,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心中唯一的神祇。
他不敢再奢望与那个世界有任何交集。他正在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由龙蛇与泥沼铺就的道路。他只希望,他守护的那个人能永远走在阳光下,永远不要回头,看见他如今的——这副模样。
又过了半年,他终于拼命攒够了一笔足以安家的钱。他为父母在工业区外围一个相对安静的小区里,租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置办了全新的家具。
做完这一切,他再次走进了那个公共电话亭,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依旧带着愁苦。他听着母亲的絮叨,等她说完,平静地开口:“妈,爸,你们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吧,来我这里生活。”
母亲愣住了:“这……这怎么行?咱们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
“一辈子,”陈东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力度,“你们在那边过的是什么日子,别以为我不知道。爸的身体需要换个暖和的地方养养,你也别再看那些邻居的脸色了。”
父亲在旁边抢过电话,固执地吼道:“我哪儿也不去!死也要死在钢城!”
“爸,”陈东沉默了片刻,声音放缓了,“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腿受伤,你背着我,在雪地里走了十几里路去医院?你说,只要我能好好的,你做什么都愿意。”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现在,轮到我了。”陈东说,“我在这边都安排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管,过来就行。就当是……儿子求你们了。”
那句“儿子求你们了”,彻底击垮了那个老工人最后一点顽固的自尊。电话那头,传来了父亲压抑的、苍老的哭声。
挂掉电话,陈东站在喧嚣的街头,看着南方城市永不熄灭的霓虹灯,心中一片茫冷。
他终于凭着一己之力,将父母从那个正在下沉的、冰冷的故乡连根拔起。但他知道,从父母登上南下的火车那一刻起,他和李怀今之间那根最微弱的、连接着地理和亲缘的线,也将被彻底剪断。
从此以后,李怀今的世界里再也不会有任何关于他的、确切的消息。而他将背负着一个家庭的未来,在这片更加广阔、也更加凶险的江湖里,继续潜行。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