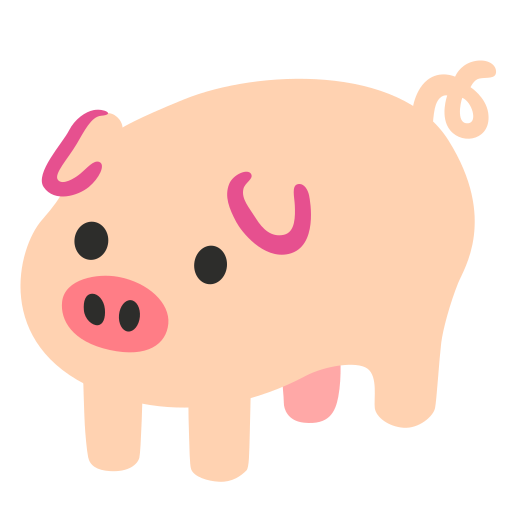15/ 浮光 掠影
编辑时间是最好的磨砂玻璃,它不会让往事消失,只会让轮廓变得模糊。
那个藏着秘密的铁盒,他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不是遗忘,而是刻意的尘封。他强迫自己不再去回想那个雨夜,不再去默念那个地址,他以为只要不回头,那些呼啸的往事就追不上他。
直到李怀今大三刚开学那年,接到了一个彻底斩断他与过去最后一丝联系的电话。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在惯常的嘘寒问暖之后,母亲像聊起一件寻常的邻里八卦般说道:“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原来的老陈家?去年冬天就搬走了,房子也卖了。”
李怀今握着电话的手,瞬间收紧,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听到自己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声音问:“搬走了?去哪了?”
“听说是他儿子陈东在广东那边发了财,就把老两口都接过去享福了。你说那孩子……“
母亲后面再说了些什么,李怀今已经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他脑子里只剩下“彻底不回来了”这几个字在反复回响。他挂掉电话,在宿舍楼下的公共电话亭里站了很久,直到双腿都有些麻木。
那个他珍藏在铁盒里的、早已失效的地址,从这一刻起,变成了一张真正的、毫无意义的废纸。他与陈东之间那根最脆弱的的线,被彻底剪断了。
从那天起,他更加沉默。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专业课和实习中,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试图将自己的大脑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知识堡垒,以此来抵御那灭顶而来的、巨大的空虚。他告诉自己这样也好。陈东有了新的生活,他也该彻底放下过去,奔赴自己的前程。他们本就是殊途,如今不过是各自走得更远了些。
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
直到那个深秋的午后,一场猝不及不及防的幻觉,将他所有的伪装击得粉碎。
那天,他刚从图书馆出来,准备沿着苏州河边的步道走回学校。河水是浑浊的灰绿色,载着几艘运沙的驳船缓缓流过。对岸是老旧的仓库和民居,充满了颓败的、属于上个世纪的市井气息。这种景象,总能让他想起家乡那条铁锈色的河流。
就在他出神之际,一个背影毫无征兆地闯入了他的视线。
那人走在他前方十几米处,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身形高挑而挺拔。
李怀今的心猛地一颤。
不可能的。他对自己说。他已经走了,离这里有几千里远。
可是,那个走路时左腿极其细微的停顿,那个对周遭一切都漫不经心的步伐,那个微微扬起的、带着一丝倔强味道的后颈……记忆像失控的潮水,瞬间冲垮了他用理智筑起的所有堤坝。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倒流了五年。周围喧嚣的闹市瞬间褪色、失声,变回了钢城那个飘雪的、寂静的黄昏。他看见的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路人,而是那个沉默地走在他身前、为他挡开所有恶意的少年。
李怀今的呼吸骤然停止,血液在一秒钟内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在四肢。他所有的冷静和自持土崩瓦解。他知道这也许是幻觉,是自己思念过度的产物。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他像一个梦游者,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跟了上去。他甚至不敢呼吸得太大声,生怕一点点的响动,就会惊碎这个来之不易的梦境。
那人拐进了一条小路,走得不紧不慢。李怀今也跟着拐了进去,心脏越跳越快。他跟着那人走过了一个菜市场,穿过了一条晾满了衣服的弄堂。那背影是如此真实,真实到李怀今甚至能想象出他转过头来时,那双黑沉沉的、带着一丝嘲弄和温柔的眼睛。
终于在一个小卖部门口,那人停下了脚步,似乎在等什么人。
就是现在。李怀今深吸一口气,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向前走去。十米,五米,三米……他能听到自己因为紧张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陈……”
那个名字刚要冲口而出,那人仿佛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缓缓地转过了身。
一张完全陌生的脸,映入了李怀今的眼帘。
那人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五官普通,眼神里带着一丝被陌生人靠近的、寻常的疑惑。他看着李怀今,问道:“侬寻人啊?”
一口标准的上海话。
轰然一声,李怀今脑中那根紧绷到极致的弦应声而断。
世界恢复了声音和色彩。菜市场的喧闹,弄堂里的市井声,小卖部里收音机的声音,潮水般地向他涌来。他看着眼前这张陌生的脸,又看了看他那条完好无损的左腿,才发现所谓的“习惯性停顿”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原来,真的是一场幻觉。
“……对不起,”李怀今的嘴唇翕动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干涩的字,“我认错人了。”
他几乎是落荒而逃。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学校的,只觉得浑身冰冷,力气被抽干。那场短暂的、由他自己一手编织的幻梦,在破碎的瞬间带走了他所有的温度。希望的出现,让绝望变得更加具体,也更加残忍。
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他没有开灯。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然后,像是被抽走了所有骨头一样,缓缓地滑坐在了地上。他缓缓地打开了那个上锁的铁盒,没有看那些未曾寄出的信,只是拿出了那张被摩挲过无数次的、写着地址的纸条。
他盯着那行早已模糊的字迹。
陈东,连同他的家人,已经像一滴水一样,汇入了这个国家南方那片由上亿流动人口组成的、名为“江湖”的海洋。没有坐标,没有航向。
他这才承认,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所谓的“尘封”不过是自欺欺人。陈东这个人,早已不是一段记忆,而是长在他骨血里的一根刺,看不见,拔不出,却时时作痛。
这场浮光掠影般的错认,像一个残酷的提醒,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单向的思念是一场无期徒刑。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看着手里的废纸,一个念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更加坚决地,在他脑海里成型:
他不能再站在岸上,等待着那滴水自己出现。他必须亲自造一艘船,驶进那片海洋。
- 0
- 0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