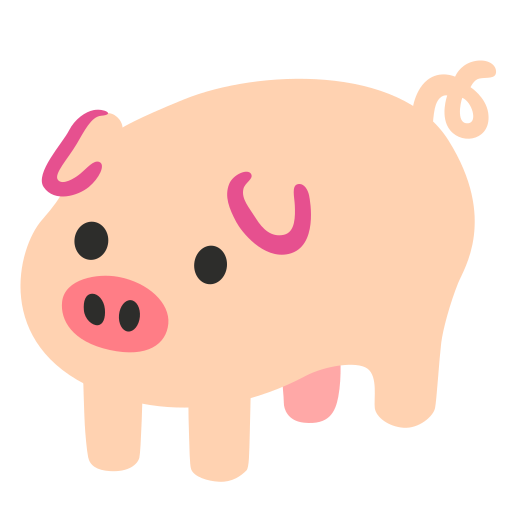Ex296/ 绝响
编辑楚王熊今是在血与火中登上王座的。
时值战国末期,七雄并立,而西边的秦国已如一头饥饿的巨兽,对六国虎视眈眈。楚国地大物博,文化瑰丽,却也因贵族倾轧、朝政积弊,显露出末世的颓唐。熊今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以雷霆手段从几位耽于享乐的兄长手中夺下了这顶沉重无比的王冠。
他富有才华,也生性多疑;他渴望建立不世之功,却又在骨子里深植着楚人特有的、浪漫而耽溺的文艺气质。他的一半是君王,一半是诗人。而这两半,日夜在他的身体里交战,让他活成了一座孤岛。
直到他遇见子期。
那是在他登基第三年的南巡途中。洪水过境,难民遍地。在一处临时搭建的粥棚外,他看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年。那少年不过十三四岁,怀里死死抱着一张被水泡得变形的古琴,因为抢夺一个发霉的馒头正被几个成年流民殴打。
他没有哭喊,也没有求饶,只是用身体护住那张破琴,眼神像一头濒死的幼狼,凶狠而绝望。
熊今鬼使神差地让卫队长救下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熊今居高临下地问。 “……期。”少年吐出一口血水,声音沙哑。 “为何宁可挨打,也要护着一张废琴?” “琴不是废的。”少年抬起头,第一次正视眼前的君王,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淬了火的骄傲,“是你们不懂。”
熊今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同样骄傲、同样不被世界所理解的、孤独的自己。
他将子期带回了郢都。
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子期确是百年不遇的音乐天才。不过数年,他便凭着一双能令顽石点头的妙手和一颗七窍玲珑的慧心从一众宫廷乐师中脱颖而出,成了熊今的首席琴师,也是……唯一的知音。
王宫的生活并未磨去子期骨子里的野性,反而将其沉淀为一种更加内敛、也更加致命的魅力。他依旧沉默寡言,依旧眼神明亮,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被宫廷礼仪精心打磨过的、近乎于完美的优雅。
熊今为他在宫苑最僻静的活水之畔建造了一座亭台,遍植翠竹。亭中不设任何象征王权的仪仗,只有一张琴,一局棋,一壶常年温着的酒。亭子落成那日,正逢连绵春雨,熊今便赐名“听雨亭”。
这里是整个楚国唯一能让“寡人”变回“我”的地方。
一日,雨夜,君臣二人再次对坐亭中。熊今刚从一场冗长而乏味的朝议中脱身,眉宇间满是无法掩饰的疲惫。
“王上,还在为与齐国盟约之事烦忧?”子期为他斟满酒,轻声问道。
“齐人贪婪,秦人虎狼。这天下,早已是一盘死局。”熊今饮下酒,目光投向亭外无尽的雨幕,“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竹子。风来,雨来,它们只需顺应天时,摇摆便是。而君王,却要逆天而行。”
子期没有说话,只是起身走到琴案前,缓缓坐下。 他拨动琴弦,一曲悠扬开阔的《高山流水》从他指尖流淌而出。那琴音时而如山峦巍峨,时而如江河奔腾。它驱散了亭中的愁绪,构建出一个远比现实江山更辽阔、更自由的世界。
熊今静静地听着。他看着烛火下子期那张专注而绝美的侧脸。他想,这世上若真有神明,或许也不过就是这般模样吧。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
“子期,”熊今忽然开口,声音低沉,“明日,你替寡人写一首赋吧。” 子期微怔:“臣,一介琴师,怎会作赋?” “你会。”熊今的眼神,变得深邃而滚烫,“你就写,寡人昨夜在此亭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位神女,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她‘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夜夜阳台,来会楚王。”
子期瞬间明白了。 他的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
君王,要为他们这段不能宣之于口的禁忌之情编织一个华丽而安全的谎言。他要将他藏进一个神话里。
“王上……”他想拒绝,他想说这太大逆不道。
“这是王命。”熊今打断了他,语气里是君王不容置喙的威严。但那威严之下,却藏着一丝近乎于哀求的脆弱。
子期看着他,看着这个背负着一个庞大帝国、却只能在梦境中寻求片刻喘息的男人。他最终缓缓地叩首在地。
“臣,遵旨。”
由子期执笔、托名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很快便传遍了七国。天下人都艳羡楚王的文采风流,与那梦中神女的旷世奇缘。郢都的贵族们纷纷在自家的园林里修建仿照听雨亭的建筑。一时间,“巫山云雨”成了楚国最风雅的代名词。
熊今的目的达到了。他成功地为自己这份危险的爱披上了一件诗意的、不容置疑的华美外衣。他与子期的每一次相会都有了最好的借口。
但他低估了政治的险恶。
他将子期捧上了神坛,他的政敌便有本事,将这位“神女”变成“妖孽”。
以丞相为首的保守贵族势力本就对熊今的诸多新政心怀不满。他们开始在朝堂内外散布流言。他们公开赞美《神女赋》的辞藻华美,私下里却将“神女”与“男祸”、“妖臣”划上等号。他们说,大王为修建听雨亭,耗费国库,劳民伤财;说大王沉湎于“神女”的靡靡之音,荒废了朝政。
更致命的,是秦国的离间。
秦相张仪入楚,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劝说熊今与齐国断交。熊今被一时的利益蒙蔽,信以为真,最终落得个背盟失地、沦为天下笑柄的下场。
国之大辱,总要有人来承担罪责。 满朝文武竟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从不干政的子期。
他们说,是“神女”迷惑了君心,才让大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听雨亭,这座曾经被誉为“风雅”的建筑,一夜之间成了“亡国之音”的源头。
连熊今的王后都深夜跪在他的寝宫前,泣血叩首,恳求他为了楚国的江山社稷,为了太子的未来,驱逐子期。
熊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那段时间,子期的琴声彻底变了。不再有《高山流水》的超脱,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悲愤与绝望的《国殇》。他为国之伤,也为己之伤。
终于,在一个风雨欲来的傍晚,他向熊今提出了那个他早已想了千百遍的请求。 “王上,送我走吧。”
熊今沉默着,为他斟满一杯酒,然后又为自己斟满。
“若我今日送你出宫,”他看着子期,一字一顿地问,“明日,他们便会逼我送出太子去秦国为质。后日,便是割让城池。子期,你告诉我,君王的退让,可有尽头?”
子期无言以对。
“我不会让你走。”熊今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用一种近乎于残忍的温柔抚摸着他的脸颊,“这座宫殿,你我一同进来。要走,便一起走。无论是走向那至高的王座,还是走向……那焚城的烈火。”
一语成谶。
三年后,秦军攻破楚国数座重镇,兵锋直指郢都。秦王假意议和,邀熊今亲赴秦国武关会盟。满朝文武皆知这是陷阱,却无一人敢劝阻,甚至有人暗中与秦国勾结,巴不得这位让他们失去权力的君王一去不回。
熊今知道自己此行,九死一生。
临行前夜,他没有与王后、太子告别,也没有召开任何军事会议。他遣散了所有人,独自一人走向了听雨亭。
他要与他的“神女”做最后的告别。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告别,而是背叛。 丞相联合禁军统领,以“楚王临阵脱逃,意图叛国”为名悍然发动了宫变。他们要的不是一个可能被秦国羞辱的王,而是一个能被他们彻底掌控的、听话的新王。
听雨亭被数千叛军围得水泄不通。 昔日的人间仙境转瞬成了绝地死囚的牢笼。
亭外,火把的光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 亭内,只有一灯如豆,和两个早已知道结局的人。
“王上,您后悔吗?” 同样的问题,在相似的雨夜,子期又问了一遍。
“不悔。”这一次,熊今的回答无比坚定。他为子期斟满酒,“寡人此生,憾事良多。唯独不悔遇见你。”
子期笑了。那笑容像雨后初晴的天空,干净而纯粹。
“能为王上弹一生琴,子期……亦了无遗憾。”
他重新坐正,将双手安放在琴弦上。他抬头望着熊今,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毫无保留的爱意与决绝。
“王上,子期为您,奏最后一曲。” “此曲,名为……《神女》。”
琴声,在这一刻,响彻夜空。
那不是《高唐赋》里,那个缥缈、柔美的仙子。 那琴音,炽热、决绝、骄傲、无畏。它用音符为那个被世人误解了的“神女”写下了最真实的注解。它讲述了一个卑微的生命,如何因为一份不容于世的爱,而变得比神明更强大,比死亡更高贵。
亭外的叛军都听得痴了。他们从未听过如此动人心魄的琴音。那琴声里没有求饶,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超越了生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就在琴声抵达最高潮的那个瞬间,一支火箭呼啸着射中了亭子的飞檐。
大火轰然而起。
熊今走到子期身后,从背后将他紧紧地、紧紧地拥入怀中。他将脸埋在他的颈窝里,嗅着他身上熟悉的、混合着木香的气息。
子期的最后一个音符稳稳地落下。 随后琴弦因为抵不住烈火的高温,发出“铮”的一声,断了。
绝响。
“子期,”熊今在他耳边,用尽一生的力气,轻声说,“别怕。这一次,我们……同归。”
他感觉怀中的人,轻轻地点了点头。
大火吞噬了整座亭台,将那段被正史抹去的、属于楚王与伶人的绝恋,烧成了一捧无法辨认的灰烟。 只留下一段关于“巫山神女”的、充满了误解的传说,和一个被铭刻在青铜器上的、孤零零的“期”字,在漫长的岁月中,等待着一场千年之后必将抵达的重逢。
- 0
- 0
-
分享